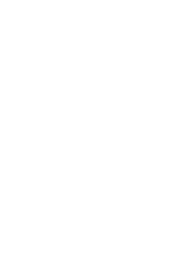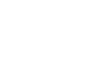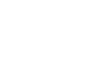此前对云冈石窟的诸多“价值”,在《云冈石窟文化》中作过阐述。七八年前的观念在当时来说颇有“新意”,但毕竟那时是在云冈石窟处于“寂寞”境况下,所言不过是一家之“孤鸣”。
自去年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以来,人们对云冈石窟可以说刮目相看了。自然许多有识之士关注云冈石窟的问题,特别对云冈石窟的价值品评,最为热衷。议论中触发我重新思考了云冈石窟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等许多问题。今应约撰写此稿。
就历史价值而言,曾把云冈石窟归结为“北魏王朝的历史博物馆”,近年来已有不少共鸣,立论总算勉强成立。然而总觉得有些单薄。盖因云冈石窟与北魏王朝的历史之间毕竟是间接关系,直接地用云冈石窟反证北魏历史,还不能达到水乳交融的境地,还缺少环节。更何况对云冈石窟在世界历史中应有的地位还属于空白。本文拟就这些重要环节再作思考,以期进一步论述云冈石窟的历史价值。
就艺术价值而论,是研究云冈石窟者最为关注的命题,近百年论述中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突出的如:从“抄袭犍陀罗说”到否定“抄袭说”,并认识到它是独立的“云冈风格”,可谓成绩斐然。但尚少具体的实例以证明何者为云冈风格,更少归纳出云冈风格的若干条目,以致评价其艺术价值时总显得若即若离。本文拟举几点实例以确定云冈风格,并论证它在艺术领域中确实是独树一帜的,并据此而品评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
云冈石窟的历史价值
近年来讨论云冈石窟的历史价值,都从附会北魏王朝的历史着眼。殊不知反映北魏历史仅仅是云冈石窟的隐形内涵,而且所含的历史成分又相当复杂,所以直接用云冈石窟去对应北魏历史总觉牵强。因此必须由表及里地逐层剖析,才能剥出其历史面貌。
应当明确,云冈石窟建造的立意不是为了记载历史,而是为了弘扬佛教,潜在地反映一些历史乃是其“附加值”。但是由于云冈石窟建造于北魏一朝(这是云冈石窟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浓郁的时代特征、鲜明的社会背景、独特的民族风格,自然格外显眼地反映在石窟中,于是在佛教的表象后面就有了深厚的历史属性,同时也就派生出历史价值。
但是,从历史角度看云冈,首先要看的是佛教的历史。其次才是北魏王朝等派生的历史。
(一)北方佛教史
云冈石窟所显示的北方佛教史,是直接的,既可靠又深厚,是对稀缺的北方佛教史重要的“补缺材料”。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史,在南方僧人的纂著中,偏重南方,并有意舍弃北方佛教的事迹,而北方僧人又无佛教史的著作传世,致使北方佛教几乎空白。近世研究或编写中国佛教史者,局限于传统,又困于史料及文献之匮乏,对这段史实也只好阙如。而云冈石窟真实地记录着北方佛教的活动,保存着实物资料,本身就是一部绝妙的佛教史,却被忽略了。这里粗浅整理,至少能够拢出下列史料:
1、北方佛教得到政权的承认,而且受国家机构的领导(道人统、沙门统)。有庞大的僧团组织。
2、北方佛教由于礼拜皇帝,必然创立了完善的礼拜仪式,也促成了宗教仪规的完备,特别在“礼佛”兼“礼拜皇帝”仪式上应是相当讲究的。
3、北方佛教徒是重视佛教义理研究的,北台译经场就有深厚的建树,特别对大乘佛学有独到的见解。并非像南方僧徒所说的“不明事理”。
4、北方有造诣很深的民问居士(邑义信士女)。
5、北方佛教僧团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寺院经济)。
6、北方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上述诸项在云冈石窟中都有所表现和反映。可是我们今天在能见到的《中国佛教史》中,却看不到这些。
譬如,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认为:
“南北朝时期,南朝重义理,人们喜欢理论研讨。北方重实践,对理论研究不像南朝人那样有兴趣。这在佛教宣传方面,也有所表现。北朝石窟造像,规模宏伟,数量众多,这也是北方重实践(造像积功德,是宗教实践之一)的证明。”①
明显地把石窟造像归结到“实践”,只见其表不见其里,这已经是近百年来通行的说法。此说根深蒂固,溯源可由梁启超先生之《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为嚆矢。他说:
佛教发达,南北骈进,而其性质有大不同者。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南方为社会思潮,北方为帝王势力。故其结果也,南方自由研究,北方专制盲从。南方深造.北方普及(此论不过比较的,并非谓绝对如此,勿误会)。②之后论述北魏佛教者大都沿袭上说,但是全都忽略了梁先生自己在括弧中的解释,而误会了下去。这种“误会”自梁先生1920年撰文至任继愈先生20世纪80年代编辑《中国佛教史》,中间有吕澄、汤用彤等众多大师近百年的阐述,还是“误会”了下来,于是基本形成“定论”。不过这种认定是有历史根源的,自南梁僧佑在《出三藏记》、《弘明集》中对北方佛教的“歧视”流传之后,就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崇南抑北的风气,所以南梁慧皎在《高僧传》中连堂堂北魏道人统法果、师贤等也不录,就连名噪一时的昙曜也只附录在《玄高传》中,充分显示出对北方僧徒的鄙夷。尽管慧皎自以为:
“自前代所撰,多日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记;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③
其实《高僧传》中有名无实者、攀附权贵者,比比皆是。所以自南北朝时始,“南北之偏见”就已形成,历经隋唐宋元有增无减,以至形成根深蒂固的重南轻北之“中国佛教史”。近代汤用彤先生似曾力求平衡偏见,但也未能扭转。他说:“北朝道佛之争根据在权力。故其抗斗之结果,往往为武力之毁灭。南方道佛之争根据为理论。而其争论至急切,则用学理谋根本之推翻。”④
尽管说的很客观平和,但把矛盾集中在“权力”与“理论”本身就是偏见。南方何尝少权力,北方又何尝无理论?道、佛之争岂能分清权力与理论?北方灭佛,不能脱离道教寇谦之为太武帝正名为“太平真君”的理论,而当时佛教的理论却没有跟上这种“世俗化”;南方佞佛(谈玄理),也摆脱不了东晋权相桓玄拍板“沙门不敬王者”,梁武帝“舍身铜泰寺”等权力。
云冈石窟,起码可以证明中国佛教史有四个方面的不足:
首先,云冈石窟建造的本身就是有理论根据的。他以佛教的大乘信仰,依据《华严》、《法华》、《弥陀》、《维摩》等经义理论,融会儒家思想,精心构筑了石窟造像。不仅使佛教作为“像教”有了宏伟而永固的偶像,而且把大乘思想充分表达于直观视觉,特别是把儒家思想贯穿到整个佛教领域,从而得到政权的认可,补上了一时落后于道教的“世俗理论”,使北方佛教由颓势变为旺势,并给隋唐佛教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就展不出北方佛教的义理底蕴,那就不是“重实践”所含的不重义理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昙靖在“北台”(在云冈)译出(实为著作)的《提谓波利经》,是以后中国佛教赖以发展的基石——佛教的儒化。尽管南方佛徒斥之为“伪经”,但也阻挡不了它的广为流传。而云冈石窟则是按照该经之儒化的“尊卑上下”、“纲常伦理”、“昭穆序列”刻出的。这不也是“义理”的运用吗?
其次,北朝有过不少的高僧,仅营造云冈石窟就必有许多。然而载入南方僧人所著之诸《高僧传》者却寥寥无几。难道北方这些“重实践”的僧徒就不值得列入《传》中?云冈石窟的存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可惜文献不录,这些高僧也就湮没无闻了。今天人们除了知道昙曜之外,对别的僧众知之甚少。有人正在探索,一旦探索有成,就能完善佛教史。
第三,云冈第11窟有太和七年造像铭一方,记录着当时“邑义信士女”53人的发愿文,这方碑碣以虔诚的信仰理念、流畅的文章,表述了造像的心愿,并成为以后石窟造像铭的范本。这就又为北方佛教史开启一方领域,即北方佛教不单是皇家的,民间的僧徒、居士也占一席之地,或更胜于南方。
第四,隋唐佛教的宗派蕃衍,其根源、祖庭有不少出自北方。1、玄高、昙曜都是习禅高僧,对禅业有很大贡献,对禅宗是否也有奠基作用?达摩的“禅”不也掺入玄高的“禅”吗?2、云冈石窟以“华严”、“法华”为主题造像,并对《华严经》有许多注疏,那么后来的“华严宗”是否应溯源于北方?3、云冈石窟中“杂密”题材的出现,及“禅密”禅法的初创,是否意味着为后来之“密宗”培植了温床?4、云冈石窟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向往,以及对阿弥陀佛的笃信,是否即“净土宗”的祖根?
上述四点至今是中国佛教史简略的地方。注意云冈石窟的佛教史料,就能为研究北方佛教拓宽领域,就能给中国佛教史填补空白。其价值不菲。
(二)北魏王朝的历史
云冈石窟在国内大型石窟中是少有的完成于一个朝代的石窟群。若把敦煌石窟、龙门石窟比作“历史长卷”,那么云冈石窟正可比作“断代史”。这个“断代”就是北魏。
为说明其断代,首先需要确定云冈石窟的建造年代,界定其上、下限。
关于云冈石窟的建造年代,近百年来专家们作了多方考证。考古学者根据造像的艺术风格,结合史料,以“和平初(北魏文成帝460)”昙曜造像为始,分为早、中、晚三期,个别窟像延续至隋唐。历史学者对开凿年代,根据文献提出“神瑞(414)”“兴安(452)”“和平(460)”三说(这三个年号都在北魏),对结束年代则依据唐道宣《大唐内典录》之“始于神瑞,终于正光”说,而定为“正光”(北魏孝明帝520——525),这就框定在北魏一朝。“神瑞”是北魏明元帝年号(414—415),由于至今在云冈石窟找不到遗迹,人们多持否定态度。我曾对《内典录》之“神瑞”考订是“天瑞”之误,而“天瑞”又只出现在《南齐书》,再考“天瑞”乃北魏道武帝“天兴”(398—403)之废年号,于是就提出“天兴”为云冈始肇说。那么这就把云冈石窟扩大到北魏整个一朝。即398--525年是其建造年代。这120多年的时代,是云冈的时代,也正是北魏的时代。时代赋予了历史使命,云冈是历史的产物,它必然要反映历史。
从历史的角度,把云冈石窟的“分期”作如下整理:
道武帝建一个窟——第3窟。
明元帝奠基二个窟——第1、2窟(有“明元始兴通乐”之说,据考通乐寺在1、2窟前,而该两窟的开凿当在后期——即老古学昕谓的第三期工程)。
文成帝建五个窟——第16、17、18、19、20窟(即昙曜五窟)。
献文帝建三个窟——第11、12、13窟。
文明太后建四个窟——第7、8、9、10窟。
孝文帝建二个窟——第5、6窟(太和八年迁都后皇家工程停止)。
景明(500)“解禁”后平城遗老修第4窟,并在第3窟内补造尊身佛像。
自“和平”至“正光”——第20窟以西之民间工程,延续不断。
这个“分期”是按帝系顺序划分的,能比较概念清楚地标明云冈工程的年代界限。不过由于文献阙如,一时尚难达到共识。但是只要找准几个“着眼点”,云冈石窟的历史价值就可以展现。
第一个着眼点就是第3窟。这个窟有一连串的问题:到底这个窟是谁开的、是什么时候开的、是怎么开的、为什么这个窟形那样的不规范?这些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自日本学者臆断为“隋炀帝为其父折冥福”而开凿,中国学者也有附和者,还有断为“初唐”者。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使原本就迷雾重重的云冈石窟更加扑朔迷离。
当另辟蹊径,考订了“神瑞说”的错误后,“天兴”开凿的说法,使问题有了突破。于是产生了以下结论:第3窟,乃是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令第一任道人统法果和尚,为僧徒们安排的居住(或习禅)的场所,于天兴元年(398)建成。它之所以能当年完工,是利用了一个天然洞窟稍加修整而成。所以形状是顺其自然而成者,不尽符合“石窟”规范(当时也没有造石窟的意识),但意外地或有意地开成了一个“大石室”,倒符合了鲜卑人崇拜石室的习尚。于是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从民族角度,这个洞窟就有了“灵”气。而后第二代明元帝祈祷于武周山(云冈石窟所在之山)就有了张本。而后昙曜选武周山开凿昙曜五窟,也有了依据。再以后把这里称之为“灵岩寺石窟”,就充分显示了外来的宗教与本土民族的原始崇拜,在“神灵”信仰上的结合。于是这个第3窟就这样以“神灵之空窟”,岿然独尊地在武周山雄踞百年。并在文献帝后的一段时期兴建窟前寺庙时,赢得在窟前构筑面阔十一间的“灵岩寺”,还成为当时对云冈石窟的尊称——“灵岩寺石窟”。至于窟内的三尊佛像则是在迁都十余年“景明解禁”后,平城遗老为怀念反对迁都的废太子元恂而补刻的。(目前此说尚属于“一家之言”)。
对第3窟的这种种判断如果成立,则对散见于史料及文献的记载就能联成一系而成为信史,并能拂去许多历史的朦胧而使面目清晰起来。那就是:北魏前两代皇帝都信佛。道武帝令法果建造的耆阁崛山(此为梵名,译为灵鹫山的尊崇在于山洞,又符合了鲜卑人崇拜“大石室”的史实)。太武帝遣使祭祀嘎仙洞也有了呼应。武周山之所以成为灵山有了依据。明元帝数次祈祷于武周山并列为“常祀”,正是因为有这个“洞”。“灵岩寺石窟”也是依靠这个“洞’’而得名。云冈石窟开凿年代要比公认的“和平说(460)”早62年(天兴元年398)。可以确定云冈石窟与北魏王朝同始终。等等。
这一点的历史价值在于能为正史作印证。
第二个着眼点是帝王象征问题。文成帝复佛伊始就明令造石像,且“令如帝身”。到在昙曜开窟造像时这自然是不成文的法规,那么昙曜开五窟、造五像是为哪个皇帝?日本学者依前任道人统师贤为“太祖以下五帝造丈六金像”故事,判断昙曜五窟也是如此。但由于说服力不强,中国学者又提出许多不同的对应,可是都没有得力的证据,谁出说服不了谁,以致众说纷纭,数说并存,把一个应当解决的问题复杂化了,并且影响到昙曜五窟以后的窟像对应。但是“佛帝合一”,一佛像象征一帝王,却是一个无争议的共识。所以不论如何对应,这里面的帝王历史是存在的。今天虽然还说不清,但并不影响用于分析历史。如果用上述历史分期去思考,北魏在平城时期的六帝、一太子(恭宗晃)、一太后,就都在云冈石窟有地位,而且包含着一段隐蔽的历史。这一点历史价值在于可以揭示宫闱隐秘。
第三个着眼点是佛经典故与社会现实的比照问题。云冈石窟的五方佛、三世佛、过去七佛、两佛并坐、维摩论辩等,反映的是什么现实问题?多年来“三世佛说”把社会问题引向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轮回”的观念上,虽然也有些帝系传承的用意,但很淡。当分析到后出的“过去七佛”时,就不得不着重考虑世代传承的内涵了。再回头看三世佛表现的帝王体系,就显得非常笼统而且含糊:倒不如五方佛,既能从空问方位上各显特色,还能用“禅观”之“五智转识”排定的顺序,一方面展示鲜卑各代帝王开疆扩土各辟一方的功绩,另一方面显示帝统传承的序列。至于以后用“两佛并坐”象征太后摄政;用“维摩论辩”标明北朝重视佛教义理;用“过去七佛”之“佛统”直接象征北魏帝系之“帝统”等,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尤其发展到太和年间,又出现以五方佛、十方佛象征皇后体系,以过去七佛(取代了五方佛)象征皇帝体系的新观念出现(见第6窟),使佛教理论与社会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而且更逻辑化了。云冈石窟的内涵也更加丰富了。同时反映出云冈石窟与北魏王朝的命运是同步的,太和年间同时进入鼎盛时期。
这一点历史价值在于从侧面记录北魏历史,并显示其兴衰。
第四个着眼点是对民族关系的反映。鲜卑族以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北部,形势迫使它不仅与汉族发生碰撞、融合,而且与其他少数民族也发生碰撞与融合。当时对北魏王朝威胁最大的是北方的柔然族(或称茹茹,鲜卑人称之为蠕蠕)见诸史籍的多为战争(碰撞)而少和解(融合)。云冈第18窟却有一方“大茹茹”残铭,记录了一段柔然族礼拜云冈石窟的佳话(今考此铭可能刻在延兴至太和年间471~492),从侧面反映出孝文帝延兴元年至太和十六年那一段不太明显的与柔然人和平阶段,虽然两次和亲不成,但使节的往来在首都平城还是有了实证。柔然人能为他们的可汗、可敦,礼拜云冈石窟,并勒铭留念,是难得的实物、文献资料。
这段历史价值在于突显民族融合,云冈石窟甚至还是融合的纽带。
第五个着眼点是对民俗风尚的记录。北魏平城时代都城的民情风俗,文献几乎空白,而云冈石窟却给我们留下至少有两处蛛丝马迹。一是,第11窟的“太和七年造像铭”及其像龛,此中记录了平城的“邑义信士女”对佛教的信仰状况与研习义理的活动。有以为“邑义”就是一种民间居士们的佛教组织,那么当时的这种组织就有相当规模了,这块铭记就记录了53位“信士女”。而且能够撰写出那样恢宏的文章,显示出她们是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与佛学造诣的。这就得改变那种“北地蛮荒”的错觉。二是,第38窟的“攀缘木桩”杂技浮雕,它虽然是佛教“幢倒使”的内容,但浮雕上充分运用了民间杂技的形式,特别在这两幅浮雕中所表现的那种“伥童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挂,譬陨绝而复联。”(张衡《西京赋》写长安民间杂技娱乐景象语)的细节内容,简直如同是按张衡文章摹刻的。这不正说明北魏平城的民间文化生活,毫不逊色于汉长安!同时也与近年平城考古所发现的,都城规模及街巷里坊之与汉长安相似或相近,相互呼应。这就给北魏平城洗去“不施雕饰”之游牧荒蛮形象,而增加了文明色彩。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对北魏王朝文化的重新评价,对历来鄙视鲜卑人的那种陈旧史观,恰是一篇批驳檄文。
这段历史价值在于既填补了史料阚如的都城民情风俗,又纠正了旧史观。
第六个着眼点是石窟中的建筑雕刻。北魏时期的建筑式样,除石窟以外,其他建筑是很难见到了,云冈石窟中刻有许多塔、屋宇、城、佛龛等属于地面建筑物的雕刻,过去一直以为是艺术装饰,研究者不太重视,偶而有文提到可能的当年平城的式样,也因无法证实而淡化。幸运的是20世纪末大同东郊出土了北魏太和年间宋绍祖墓,其中有一组仿庭院式的建筑,是按照他生前居住的房屋形式构筑的,与云冈第9、10窟等的那种四明柱、三开间、一斗三升、人字拱的庭院式佛龛一模一样。这就为云冈石窟所有的建筑雕刻提供了实物旁证,证明云冈石窟的建筑雕刻是有当时的现实生活之原型依据的。更进一步可以联想,当年王遇为太后精心营造“双窟”的匠心,太和三年落成了乾象、坤德两座六合殿的那种“六合”巧思(天地四方),也在这里展现。那么看云冈,就能看到千五百年前平城建筑之一斑,这更是史料之所无。
这段历史价值在于能以实物形状,再现当年的历史原貌。
上述种种,不过是云冈石窟历史价值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还没有认识到的应该说还有很多。仅就上述已可看出,云冈石窟的历史价值是相当深厚而广阔的,他是一部无文字的“史记”。
二、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
20世纪初,外国学者发现云冈石窟时,最触动他们的心扉并引起震颤的就是“艺术”。正是因为云冈石窟艺术自身品位优越,所以无论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诗人以至科学家等等,在探究云冈石窟时,除自身专业外,大都把重点放在“艺术”的描绘上,于是形成一种谈云冈必谈艺术的风气。这种风气还波及到国内,以致连石窟考古,也是以“艺术风格”作为“长期坐标”之定位的。这就说明云冈石窟艺术之表象魅力与内在价值,足可以适应各种论说之需求。因此近百年之论述云冈石窟,成就最大的就是“艺术”,而且流派纷呈,可谓百花齐放。但是浏览百花,仍有只见其“形”不见其“神”之感。究其所以,是因尚未点明其“价值”。不过也应该看到,评价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近年大同青年教授王建舜有《云冈石窟艺术审美论》问世,是首对云冈艺术用“美学”的观点作审视者。用美学讨论云冈石窟的艺术,不仅能开拓视野,而且可以深人层次,从这个角度探讨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则“庶乎近焉”。可是目前还鲜有共鸣,如果不是曲高和寡,那就不能不说是云冈研究之“寂寞”。
时至今日,面对云冈石窟这份堂堂的世界文化遗产之艺术的认识,如果仍然停留在“瘦骨清像”、“褒衣博带”、“弥勒交脚”、“菩萨花冠”的讨论上,就未免显得单薄。更何况众多“旅行家”局限于对造型外表的直观感觉与欣赏,偏颇之语反而有损品评云冈的艺术价值。比如80年代有人说:“云冈大佛的满身疮痍,手脚斑驳所呈现的那种朦胧美,又何尝不是大自然的‘罪孽’同时也是一桩‘功德’呢?⑤”这岂不离题太远?尽管原作者还说:“从文物的角度,我们必须保护它们的本来面目,不使损毁走样;但从艺术的角度,我们毋宁更欣赏他们被‘破坏’以后的‘变相’一这实在是一个‘悖论’。”⑥可是浮光掠影地看云冈,又几个能脱离了这种“悖论”去谈艺术价值呢!那么如何讨论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
试作五个方面的探讨:
(一)云冈风格与犍陀罗风格的对比
毫无疑问云冈风格是来源于犍陀罗风格,但差异是相当大的。差异就是创造。那么云冈风格的创造何在?答曰:“在于石雕艺术的古今中外大融合。”
中国的石雕艺术源远流长,从秦汉到两晋,从石鼓文到人兽像,从线条粗犷之写义到细腻逼真之写实,从平雕、浮雕到圆雕,可谓应有尽有。到两晋时已经形成的中国“古典风格”之石刻文化,直至南北朝之前期,基本是“纯中国式的”。而正是在南北朝时期犍陀罗石雕艺术传人中国,使中国的石刻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汉晋之古典风格(浪漫风格),变为隋唐之佛教风格(现实风格)。
犍陀罗艺术,在印度也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由几种艺术的融合,逐渐形成为风格的。当希腊的人像雕刻艺术传人犍陀罗后,与本土佛教结合,创造出人形的佛陀造像,对佛教的发展还起到了推动作用,不仅改变了佛教徒的偶像崇拜方式(由过去佛徒崇拜牙爪发塔等而变为崇拜佛像),而且使佛教整体向着多神的“像教”发展。于是在创造出精美绝伦的释迦牟尼佛像后,又派生出众多的佛、菩萨之殊妙形象,从而逐渐形成一个影响极大的艺术流派。
犍陀罗艺术,是一个传播很广的艺术流派。五胡十六国时期佛教徒开始把这种艺术传人中国,先在新疆、河西走廊的石窟中,以绘画、泥塑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在北魏云冈石窟雕凿石像;再以后便在中国各地广为流传;后又传到国外。犍陀罗的石雕艺术传人中国,是中国传统石雕艺术第一次古今中外的大融合,也是中国石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云冈石窟就是这块里程碑,其特征就在于“全石化”,即无论是洞窟还是造像,都是石头的。它一改中国西部那种:石头洞窟、彩绘壁画、泥塑佛像“三结合”的石窟状况,而开创新的局面。云冈石窟的全石化,是中国石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价值就在于:既使“石窟文化”进入完善阶段,又为以后的所有石雕艺术创立了新风格。所以它的价值是划时代的。
云冈石窟与犍陀罗风格不同之处在于形象的差异。因为所有佛陀形象都是神的人格化,所以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信仰人群,都要按照他们自己的容貌塑造神像,差异也就自然形成。
犍陀罗,自马其顿亚历山大经过希波战争,赶走古波斯帝国,统治了犍陀罗后,首批“佛陀像是希腊人按照耶稣像和圣徒像的风格雕刻的”⑦。以后经过:孔雀王朝的笈多时代、帕提亚帝国时代、大夏希腊化时代、大贵霜时代、新波斯帝国时代、小贵霜时代、直至嚈哒时代,各种形式的艺术风格都汇集于“犍陀罗”,逐渐形成犍陀罗式的典型佛像。其典型的特征是:欧洲发式、希腊鼻子、波斯胡子、罗马长袍、印度薄衣、袈裟透体等之“程式化”形象。这种形象经过不断磨练,不仅延续下来,而且传播出去。
云冈石窟,自北魏“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馀步,视之出炳然,转近转微”⑧。这大约誓壁公元455—460年间,斯里兰卡僧人难提等,带到平城的三个犍陀罗佛像。从时间上看,带来的当是犍陀罗成熟的作品。正好与460年开凿昙曜五窟相衔接。同时说明昙曜在雕琢五窟大像时,是有犍陀罗佛像可以作为模仿依据的。那么,说云冈模仿犍陀罗(甚至说照抄犍陀罗),也不算过分。但是,雕凿云冈石窟的众多工匠,却不是犍陀罗的,除平城当地的工匠外,还有来自北凉、辽西、中山等地的,甚至还有高车等诸民族的,成分相当复杂。昙曜尽管可以要求摹刻逼真,而工匠们也要各抒情怀,所以不会去照抄犍陀罗像;更何况最最根本的是鲜卑皇帝要求的是“令如帝身”。这就决定了昙曜必须另创佛陀形象,不可能去照抄那三个犍陀罗像。所以形成“云冈风格”,乃是必然。
云冈风格与犍陀罗风格不同的特点如下:
首先是“肉髻”:肉髻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⑨对这个“肉髻”在犍陀罗造像中都作了发饰处理,而且花样繁多,具有代表性的是“螺髻”,即在正常头部与顶上突出的肉块处,皆弯满如同海螺一样的发髻;此外还有“卷曲式”、“波纹式”、“梳发式”、“花瓣式”、“平分式”等等,基本是按照:欧洲地中海、欧亚非交界之米索不达米亚,以及南亚一带印度等地之古人种的发式摹刻的。其实如此多样的发饰,并没有突出表现佛陀的“肉髻相”,而是服务于艺术。而云冈石窟的佛像却一反犍陀罗的发式造型,改造为“无发式的光圆肉髻头顶”,突出了头顶上的肉髻,生动准确地表现了佛陀的“肉髻相”。值得注意的是:犍陀罗几乎没有“无发的肉髻”,而云冈则又亟少“有发的肉髻”。⑩这种变化到底是为了准确表现“肉髻”,还是为了表示鲜卑人“髡发”、“索头”的习俗?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可惜现在尚未作过论证。但是云冈石窟的肉髻不同于犍陀罗是可以肯定的。这乃是构成“云冈风格”的要素之一。
第二是“鼻子”:犍陀罗雕像的鼻子,通常称之为“希腊鼻子”,是模仿希腊人鼻子的特征刻成:高直、悬垂、滚圆的形状。而云冈石窟雕像的鼻子,则以“方直鼻梁”见称(这是直观的描述),而且其“方”还相当夸张,有如刀削一般,棱角分明。于是形成“方直”与“滚圆”的鲜明反差。构成又一“云冈风格”。
第三是“眉眼”:犍陀罗风格是“高鼻深目”,眉与目眶相连,一派希腊、罗马人的模样。而云冈石窟则是“细眉长目”,特写亚洲人的特征。经过艺术夸张后的“细眉长目”,是不是鲜卑人原型?就十分耐人寻味了。今天虽然难以确证它像谁,但是“云冈风格”则比较鲜明。
第四是“耳朵”:犍陀罗雕像的耳朵特征不太明显,或许是由于“三十二相”中没有“耳相”,仅“八十种好”中有“耳轮垂埵”一好,所以仅仅把耳朵刻得厚大一些。而云冈石窟雕像的耳朵却是大得出奇,是名副其实的“两耳垂肩”像,这不仅是五冈石窟佛像最显眼的特征,而且也是中外石窟之中的绝无仅有者,就连石刻以外的泥、铜等各种佛陀造型也不曾重见,诚可谓独树一帜。要问这种耳朵在北魏平城有什么现实原型?无从考证。只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仙人两耳垂肩”的传说,可能北魏道教传播这种传说,又被佛教所接受,而留下如此一抹文化遗痕;另外就是民间传说的“三国刘备有两耳垂肩、两手过膝的福像”正好象征帝王,或被鲜卑皇帝选中。这样就给“云冈风格”添上重彩的一笔。
第五是“唇髭”(俗称八字胡):犍陀罗雕像中唇髭是显眼的杰作,把髭胡刻的很浓重,一派阿拉伯人的气派,故称作“波斯胡子”。云冈石窟雕像中带有唇髭的像较少(或因风化、或因敷泥、或原本就没刻),但是代表云冈石窟的露天大佛却给我们留下两撇漂亮的唇髭,十分清秀淡雅,不像波斯胡子那么浓重,倒像回鹘胡子那种俏皮:细细地、弯弯地、两角上翘。这就引人入胜地联想到鲜卑人是否也是这种唇髭?若是,那就又提供了一条鲜卑人的“基因”信息。不过无论是否,这撇唇髭还是表现着“云冈风格”。
第六是“脸型”:犍陀罗的脸型,属于瘦型圆脸,下颔微削,肌肉丰满而且坚实,呈现一种威武姿态,好像充分显示释迦等学之“大雄”风采。而云冈石窟的脸型,则属于胖型圆脸,下颔重颐,肌肉温润而不臃肿,呈现一种祥和亲切的姿态,表现的是释迦牟尼普渡众生之“慈悲’’形象。这既是大乘佛教徒信仰与崇拜的形象,也是鲜卑皇族希冀的自我形象,还是当年民众敬仰、喜爱的形象。创造这样的“云冈风格”,乃是必然。
第七是“立像与袈裟”:犍陀罗的佛陀立像,是承袭古印度南部“秣菟罗造型”而来,其特征是:身着长袍覆体之通体袈裟、u型衣纹、背后圆形背光、薄纱透体的特殊效应等。在犍陀罗,又把罗马长者的长袍式样融人通体袈裟,袈裟虽然增厚了,但透体的效果依然明显;又吸收了希腊的人体雕塑手法,使透露的肌体更加清晰、丰满、圆润,而成为风格鲜明的艺术造型,多为绝世精品。云冈石窟的立像风格迥然不同。昙曜的第一个立像(第16窟)就把“罗马长袍”改为鲜卑人之游牧服装,变成格外厚实的“厚重毡披”,还装饰了一条“领带”(这条领带很像今天朝鲜妇女胸前的结带,它不仅增加了美感,而且引人思考:鲜卑与朝鲜之民族源渊有无关系)。昙曜的第二个立像(第18窟)更是一尊绝妙的立像,无论从宗教内涵还是艺术效果看,都可评为举世无双之稀有珍品。云冈石窟在第11窟、第6窟,又出现中原传统文化的“褒衣博带”装,具有代表性的“七佛立像”及“佛母立像”,尽管略显程式化,但不仅不影响佛像的内在之美,还传递出一派雍雍华贵的中原华夏文明风采。云冈石窟的“立像”与“袈裟”可谓丰富多彩,其风格是鲜明的。
第八是“坐佛、佛座与手印”:犍陀罗的“坐佛”雕像,出现较晚,但是由于吸收了较多的艺术成就,加上对佛像观念日臻成熟,新创作的,右手仰掌,左手执衣襟之“说法坐佛”像,不久就成为极其普遍的一种艺术形式。佛陀的形象也趋于定型,于是就成为坐佛的定式。这种造型的特点,是在秣菟罗坐佛造型的基础上,加以希腊化而形成的。佛的形像趋向清秀:胸围略瘦,袒露右肩,斜披袈裟,施无畏手印,双腿盘曲作降魔坐(或吉祥坐),赤脚仰底、袈裟覆盖,坐于方形台上(多称金刚座)。犍陀罗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还创造出许多变形的造像,可谓琳琅满目。而云冈石窟的三大坐佛(第19、20、5窟)及无数小龛坐佛,则是统一的坐式,但与犍陀罗的坐佛模式有许多不同:手印由无畏印变为禅定印;又由说法坐佛演变出云冈式的说法坐佛、思维坐佛、禅定坐佛、转法轮坐佛、苦行坐佛等;佛的腿式多为吉祥坐(以右腿脚包押左腿脚);右袒袈裟皆不覆膝(犍陀罗多覆盖腿脚,以致难分吉祥、降魔);佛座,在金刚座之外,又创造出莲花座;等等。云冈石窟的坐佛,充满了儒家的君子之风,是表现当时鲜卑皇帝最理想的形象,所以鲜卑皇族承认它;这种坐佛,对“观佛”之禅僧能产生“安稳”感,所以禅僧需要它;民众面对这种坐佛,其心灵能融入极乐世界,而感受到祥和,所以民众喜欢它。这些都是构成“云冈风格”的背景因素。
第九是“辅助雕刻”:犍陀罗艺术还表现在佛陀以外的其他神像上。大约在贵霜王朝时期达到了顶峰。其迦腻色伽王虽然也成了佛教徒,但是他的原始信仰没有完全消除,他同时尊崇其他宗教的神祗,在他的钱币上就有许多神祗是出自希腊神话,锁罗亚斯特教,密陀罗教,以及印度教。犍陀罗造像中同样也就出现了这样的神祗。⑾犍陀罗的非佛教神像,更多的是来源于印度婆罗门教,如印度神中的因陀罗、梵天、金刚力士,以及多子女神鬼子母、水府神龙王、太阳神鸟迦楼罗、药叉、药叉女、紧那罗、乾达婆等;还有少数,属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安息民族的神那奈亚、法罗、阿德克休;来自希腊世界的神祗(与犍陀罗有着渊源久远的雏形关系)如:河神、罗马化的雅典娜、太阳神哈耳波克剌忒斯、马人刻陶洛斯、森林神西勒那斯,以及业已趋向印度化了的希腊神祗如:司农、丰饶、护婚神得墨忒耳(化为鬼子母)、担天巨人阿特拉斯、海神、小爱神阿摩耳(化为小精灵药叉)等。⑿
以上这些神祗,在云冈石窟并未完全出现。但偶尔出现的几个造像却非常生动,甚至堪称精品。比如,第8窟前的两幅浮雕,就是婆罗门教的神祗——鸠摩罗、摩醯首罗,刻得栩栩如生,它不单纯是以多头多臂烘托形象,更重要的是线条的运用和神态的表现。虽然仅仅是浮雕,却展示着中期的成熟技术,其艺术水平可以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无论是头上的花冠、尼泊尔式帽子,还是胯下的神牛、迦楼罗式神鸟,皆能留给人们许多悬念(如它与大乘有何瓜葛),这乃是前所未有的艺术境界。其他如:赤脚飞天、双跪美人、托臂力士、维摩挥尘,以及复瓣莲花、云文忍冬、覆幔佛龛、桦树、麋鹿、博山炉、摩尼珠等等,无不显示着云冈的风格,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不过这些造像在云冈石窟都处于从属地位,而且大多数出现在后期(昙曜五窟中的所有辅助像都是后来补刻的)。值得注意的是,云冈石窟在这些辅助形象的创造上,还是为“云冈风格”增添了不少色彩。
第十是“洞窟的整体布局”:犍陀罗地区的佛教胜迹,是以寺庙和率堵波为代表,石窟的形式不太典型,所以佛陀的铜、泥、石像多以单体游离。于是所渭犍陀罗艺术,集中反映在单体造像上,还谈不上石窟等之整体布局。而云冈石窟则不然,其造像的出发点,首先就是服从整体布局,然后才考虑佛的造像。昙曜之所谓“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⒀就是要表明:五个佛是因五个窟而设,绝不是为五个佛而开五个窟;开五个窟是为五个皇帝服务的,既要让五个皇帝各有领地,又要让他们在领地中惟我独尊。同时安置五个皇帝还需要有个次序,洞窟有了次序,佛也得有个系列。这就必须突破犍陀罗的那种单体造像的思路,而得有通盘考虑,于是就有了整体布局的要求。上述昙曜五窟是一组系列洞窟,它充分体现了平城佛教在灭法后的反思,它一方面汲取道教“为皇帝正名”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接受儒家思想,注入了伦理纲常,昭穆分列,尊卑有别,左右有序等内涵。昙曜运用这种新观念,巧妙地把佛教的“右旋法则”与儒家的“自右至左之顺序”结合起来,构成五窟的次序;并且使每一窟的主尊佛像成为该窟的“惟我独尊”,而窟内其他佛像都是臣民,使尊卑分明;还体现出一窟就是一个时代、一方领土,合起来又是一个传承体系。如此种种,仅从昙曜五窟,就可以看出云冈石窟之布局考究、构思巧妙。这也是“云冈风格”的一个大方面。
关于昙曜五窟的五方佛、五智如来、五智转识、五禅观(东因、中因)等论述,我在《昙曜五窟的佛名考校》⒁一文中有详话。这里概括简述如下:云冈石窟,自昙曜开创伊始,就贯穿了“大乘”佛教意识,至终未变。其主要原因就是昙曜的五窟、五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五佛就是将犍陀罗朦胧的五禅那佛具象化,即:1、东方阿閦佛一大圆镜智;2、南方宝生佛一平等性智;3、西方阿弥陀佛一妙观察智;4、北方不空成就佛(与释迦丕尼佛同体异名)一成所作智;5、中央毗卢遮那佛一法界智。依次从第16--20窟顺序排列,体现着:“东因”之“五转”,即一切众生之修菩提心者,所用的“自因至果所得之功德”,也就是:从东方一发心、南方一修行、西方一菩提、北方一涅盘,至中央一方便究竟。这样的一种循序渐进的修行方法,对于习禅僧“坐禅观佛”很适用。同时又把佛教的“右旋法则”(如日月经天东起西落)形象化。⒂这种从东到西的顺序布局,还适应中国传统文化,故而是构成云冈风格的一大要素。
上述10点,云冈艺术与犍陀罗艺术的比较,不过是其局部的具体比较,距离全面分析还相差甚远。不过通过以上对比,对“云冈风格”已可窥视一斑。
(二)犍陀罗风格的承袭与发扬
公元460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
这一年可以说是犍陀罗艺术的转折年。这一年,由于白匈奴占领了犍陀罗地区,犍陀罗艺术开始步人衰退阶段;而这一年,昙曜却在云冈石窟开始开窟造像。不仅保留了犍陀罗艺术,而且把它发扬光大,创立了“云冈风格”。从此犍陀罗艺术之花,在云冈石窟盛开。云冈石窟能保留并发扬这份珍贵艺术遗产,也是云冈石窟艺术的一宗宝贵价值。
犍陀罗的单体佛时代,好像并没有完成犍陀罗应该完成的造像体系。随着公元460年白匈奴(嚈哒)的入侵而衰落、而终止了。恰好也是公元460年昙曜在云冈开窟造像,犍陀罗的余绪似乎历史地落在云冈石窟。美国H—因伐尔特在其《犍陀罗艺术》中有一段话很值得玩味,这里录其全文备考:
“大乘佛教在迦腻色伽王时期,明显成为优势而强大起来,——在这里,我们仅能够给予一个大致的梗概描述:大乘派的中心教旨是自我创造(意为普渡),最原始的存在是阿提佛陀,意为第一觉者,他不仅靠冥思创造了世界,而且也在极费时日的深悟之下,创造出了五禅那(或称五智如来),这是智慧无比的佛,并赋予了形态。正是从这五禅那佛中,又辉射出了五菩萨,他们负有主宰宇宙局势的神力。通过禅那菩萨行,使他们影响人类,这动因是人类存在的最高升华,这便被叫做摩奴识佛。在时间周期里,佛祖悉达多正属于摩奴识佛;禅那佛则是阿弥陀佛和他的胁侍菩萨观世音。摩奴识佛既是佛祖悉达多本身,后世的继承者自然就是弥勒。”⒃
这是一段研究犍陀罗艺术者们甚少涉及的领域,尽管是否准确尚需考证,但它至少向我们透露了四条信息:1、犍陀罗极盛时期(迦腻色伽王时期)大乘佛教徒已经创造出(准确地说仅仅是在理论上提出)“五禅那佛”;2、犍陀罗已经制造过五禅那佛,即所谓“并赋予了形态”(遗憾的是在犍陀罗佛像中至今尚未辨认出五禅那佛像的个体佛名以及其组合系列);3、五禅那佛中,有阿弥陀佛;4、已经确定了弥勒是释迦牟尼的继承者。这四条,无论在犍陀罗实现与否,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却创造出来了,而且构成了一组十分完美的系列洞窟,并包含了禅观之“观佛”与“五智转识”等深奥的义理。这就奠定了云冈风格的大趋势。
公元460年这一年,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当5年前西域僧人难提等5人带着那三尊佛像来到平城时,似乎就预示着犍陀罗艺术要东移了。因为西域诸国,谁家也摹刻不出犍陀罗的那种“视之炳然,转近转微”的神态。东去以求知音,则势成必然。公元460年犍陀罗艺术终于在必然的趋势下,巧合般的在云冈石窟开花结果了。彼衰此兴,良可叹焉。公元460年的巧合深可玩味。
这里说明一点,460年昙曜造像,与398年法果开第3窟,是两个不同文化范畴。法果之窟属于“洞穴文化”,昙曜之窟与佛才进入“石窟文化”,后来在窟前建筑楼阁就加入了“寺庙文化”。这是云冈石窟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都属于云冈,但不能混淆。
(三)昙曜功不可没
昙曜在《高僧传》、《续高僧传》虽都有传,但极简略,连生平都不详。近年有考证为“罽宾沙门”者,也是证据不足。我曾根据:云冈第11窟《太和七年题记》之“苌衣改昏”和《释老志》之“御马前衔曜衣”(俗称马衔袈裟),判断昙曜是乌苌国人。着眼在:乌苌国之“阿波逻罗龙泉的如来濯衣石”上面留下的“袈裟衣纹”遗迹(《法显传》、《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大唐西域记》皆有记载,或称乌仗那国)。如果判断不误,则昙曜对犍陀罗早已相当了解。因为乌苌国紧邻犍陀罗国,昙曜青年时期,或还没来中国以前,正是犍陀罗艺术的鼎盛时期,昙曜有条件亲历、目睹犍陀罗的发展盛况。如此,则昙曜在云冈石窟承袭并发扬犍陀罗艺术,可以说渊源久远、宿因甚深。也只有他能够准确的把握犍陀罗风格。所以他能完成西域诸国所不能完成的任务(指摹刻难提传来的佛像)。那么云冈石窟承担发扬光大犍陀罗的艺术,历史性地决定:非昙曜莫属。
昙曜以其“习禅僧”的信仰,还完成了犍陀罗没能完成的艺术构想,把“五禅那佛”堂皇地刻在云冈石窟,不但继承了犍陀罗艺术,创立了云冈风格,还把佛教之教义推上一个新高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五窟既完善了“禅观”,又弘扬了大乘;既奠定了禅业,又开启了华严;尤其是把当时凌乱的“杂密”,梳理出一套系统的形象体系,把鸠摩罗什的“如来禅”推向达摩的“祖师禅”,初创“禅密”,不但能为“禅观”服务,还为隋唐密教(宗)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昙曜功不可没。云冈石窟记录着。
(四)云冈石窟艺术的审美价值
美学,是艺术的上层理论。云冈石窟不仅仅是艺术体,还蕴涵着美学。如何对云冈石窟艺术进行审美?是评定云冈艺术价值的必要尺度。至今,讨论云冈艺术的成就可谓硕果累累,而对云冈的审美探索还是寥若晨星。
王建舜教授对云冈石窟提出了三条审美价值:形成价值、心理价值、哲理价值,是很有见地的。按照他的说法:“云冈佛教石窟艺术的形式价值,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表现出多种形式因素的交融与合力。这种形式价值具体可归纳为:形式的抽象性、形式的和谐性、形式的愉悦性。”“心理价值,具体地表现为:心理的同情感、精神的趣味性、心理的潜意识生活。”“哲理价值,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僧家之哲理、世俗之哲理。”⒄这种提法,虽然还不能包容艺术审美的全部价值,但是已经触及到“艺术体”表象后面的精神实质,为品评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开阔了视野。
艺术审美,确如一曲高雅音乐,需要用心灵去聆听,非直觉之所能者。芸芸众生对云冈石窟艺术能有什么“审美”?我曾以众生窥视云冈艺术的堂奥,分别从两个角度臆测其“美”,即:创作者的“审美观”与观赏者的“美感受”。我以为凿琢云冈石窟者,至少完成了五项“美的创造”,那就是:1、佛陀、菩萨及诸神之美;2、鲜卑人之美;3、气势之美(特指云冈石窟之大窟、大佛、大气派);4、富丽堂皇与淳朴淡雅之美;5、细腻传神与粗旷豪放之美。这些,人们从直观上是能感觉到的。那么芸芸众生面对这些“美”,有何感受?曰:感受到五种“美的吸引力”即:1、景仰力;2、虔敬力;3、震慑力;4、赞叹力;5、萦绕力。的确,未来云冈者,若闻其名,无不向往;有来云冈者,无论僧俗,面对如此佛陀慈悲,多有“了却尘心,向往极乐”之念;更多的旅游参观者,则被大窟大佛大气派所震慑,似乎面对如此不可思议的佛国世界,人类世界一下子渺小了,区区个人又何足道哉;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呼出:“真了不起”、“太壮观了”……;离开云冈后,谁也都会回味好久,甚至梦绕萦迥,几番思念。冰心老人有一段话说出了大众的心声:“万亿化身,罗刻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事后追忆,亦如梦人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是啊,文字怎么能描述这种心灵的感受呢!⒅
(五)如何品评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
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具有多方面的“二重性”。
1、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既是鲜明的,又是朦胧的。其鲜明之处在于人人皆可觉察到它是艺术品,纵然品评的差异很大,那也正符合了对艺术评价的基本规律(见仁见智本来就是艺术审美的一大特色,人言人殊更是在所难免)。难得的是一件艺术品能得一公认是“美”,那他的价值就鲜明了。云冈石窟就是公认了的。但是要问它究竟美在哪里,多数人就要犯糊涂了,真有那种“口不能言,笔不能书”的感觉,此刻的云冈石窟艺术是朦胧的。朦胧价更高。
2、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具象的,人们已经从头面身体服饰装饰等,说出了许多;抽象的,则甚少涉及。盖因抽象之涵盖太广太深,令人难以琢磨。比如:佛像,究竟是佛之美,还是鲜卑人之美?厚重毡披,究竟是通体袈裟,还是鲜卑服装?褒衣博带,是佛装,还是中原传统装?两佛并坐,究竟是释迦、多宝,还是太后、皇帝?其美为谁,实在抽象。可是一旦悟出其抽象,则美不胜收。抽象价更高。
3、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既是完整的,又是残缺的。历经了一千五六百年沧桑的云冈石窟,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可以说基本是完整的,这很不容易(就世界石窟而言,难得有这样一区完整的艺术体)。但是毕竟岁月无情,云冈石窟无论从它的整体上,还是个体上看,绝大多数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残缺是绝对的,说它完整仅是相对的。可是他的艺术的光华,冲破完整与残缺的界线,处处展示着“美”。于是,完整的、残缺的都具有了价值。完整的,体现着原型之艺术价值;残缺的,留给人无限的想像空间,偶而还能构想出一种无形的价值。
4、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既是浅显的,又是深邃的。浅显,表现在人人都能看懂云冈,有意无意地受到艺术的感染而欣慰;深邃,则是越看越看不懂,到底这些佛像,何缘而为,何因而设,何所思,何所为;真身耶,假象耶;庄严慈悲为那般,凌空飞舞何所依;究竟是人,还是佛?仔细想来,其表象与内在之间,还蕴涵着许多深奥,隐藏着无限精邃。而这些玄机,都包容在其艺术形象中,并且随时透露着信息,让人自然而然地领悟着。这就叫做深浅咸宜,价值无边。云冈石窟艺术留给世界一片“永恒的微笑”。都懂!
上列,对云冈石窟艺术价值的五点讨论,仅可谓管窥一孔,绝非全豹。如果能够允许更超脱一些来谈,是否可以放眼世界,说这样一句:“云冈石窟艺术,是继犍陀罗艺术之后,在世界上惟一能够成为体系的石窟艺术流派,即云冈风格的艺术流派。”话虽然大了一些,但事实上,云冈以后的石窟,几乎都有云冈风格的影子!这一点该是云冈艺术的“宏观价值”。
本文所谈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仅只是云冈石窟价值的一部分,而且只谈到了一些皮毛,距“全面阐述”相差甚远。何况还有诸如:考古价值、佛学价值、民族价值、民俗价值、建筑价值、科学价值等,尚未涉及。惟盼大家从更多方面论考,对本文予以指正。
① 继愈《中国佛教史》第3卷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
② 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第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版。
③ 慧皎《高僧传•序录》,见中华书局校注本第525页,1992年10月版。
④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3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 徐建融《文物旅游的魅力》,载《旅游天地》1986年第6期第14页。
⑥ 同上。
⑦ 福彻尔《佛教艺术的玎端》第十六章。转引自:巴基斯坦一穆罕默德一瓦利
⑧ 乌拉一汗《犍陀罗艺术》第94页。
⑨ 引自《魏书•释老志》
⑩ “三十二相”是释迦牟尼佛区别于芸芸众生的特殊相貌,计有三十二种,佛经中有几种说法,常用的是《三藏法数》的描述,其中的第三十二个相名“成肉髻相”解释曰:“梵名乌瑟腻,译作肉髻,顶上有肉,隆起为髻形者。亦名无见顶相,以一切有情皆不能见故也。
⑾ 第16窟之阿閦佛立像头顶上有花纹,那只是花纹而非发式;第11窟之七佛立像头顶上也有花纹,仍然只是花纹,而非发式‘第5窟最大释迦佛像及两侧胁侍立像,头顶上是螺髻,但那是后世敷泥时的改装的泥螺髻,而非原石刻,其西侧胁侍立像剥去敷泥后,露出的原石刻是“无发的肉髻”,足可逻辑推断,该窟主佛的原石刻还是“无发的肉髻”。
⑿ 参阅,巴基斯坦—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著《犍陀罗艺 术》。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4页。
⒀ 参阅美—H—因法尔持《犍陀罗艺术》第12页。
⒁ 《魏书》释老志。
⒂ 载《天津师大学报》1987年第六期。② 之前中外学者对昙曜五窟作过各种排列,有白西向东者,有中央定位者,有昭穆排列者,有大窟小窟分配者,等等,都不能妥贴说明整体布局,不如此说顺通。
⒃ (美)H•因伐尔特《犍陀罗艺术》第12页。李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⒄ 引自王建舜《云冈石窟艺术审美论》144、168、1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1月。
⒅ 择自谢冰心1934年《游云冈日记》。参阅:赵一德《云冈石窟文化》第419—42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l0月。
2002年10—11月于大同宅舍
(赵一德:高级经济师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理事云冈石窟研究专家《北朝研究》前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