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由青岛出版集团、云冈石窟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云冈石窟全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以及来自国内出版界、学术界、文化界的知名学者及北大师生近200人参加了座谈会。

▲《云冈石窟全集》揭幕仪式

▲会议现场
在发布仪式上,与会领导为《云冈石窟全集》揭幕,云冈石窟研究院和青岛出版集团向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各赠送《云冈石窟全集》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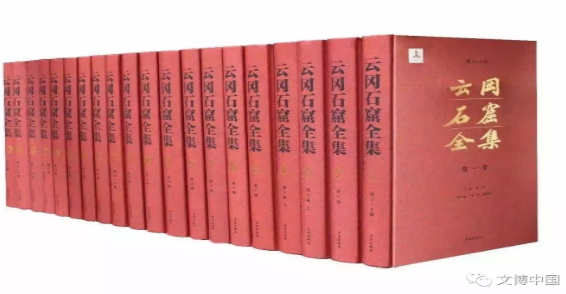
在会上,葛剑雄、丁明夷、朱青生、罗世平、余江宁、谢继胜、李军、郑岩、荣新江、汪家明、孙庆伟、杭侃等来自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史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对《云冈石窟全集》给予高度评价,从各自角度阐发了该书出版的重大意义。


▲专家座谈现场

葛剑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拿到这部巨著,我感到它达到了我们原来预期的高度。
云冈石窟这几年经过全面的保护,很多地方和我以前去看过的相比,恢复得很好。这次花这么大精力成功编纂出版这样一部书,选题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之前只有日本人做过这个工作,但当时他们的条件和我们今天是完全不能相比的。现在拿到这部巨著,我感到已经达到了原来我们一起参与时的预期,可以说是云冈石窟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最完整的、最深入的、最具体的记录。这套书尽管对我们来讲出得迟了一点,但是可能恰逢其时,如果早十年的话,照相技术、出版技术还没有这么高的水平。

丁明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出版大型的研究云冈石窟的权威著作。云冈石窟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日本学者用了16年时间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了16卷32册的《云冈石窟》,代表了当时云冈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是云冈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历史。从那时起,云冈人挥之不去的使命担当就是如何做出一部中国人自己的、超越日本《云冈石窟》的巨著。这个使命在刚刚出版的20卷《云冈石窟全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云冈石窟全集》的问世是云冈研究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是云冈人打的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朱青生(北京大学教授)
《云冈石窟全集》出版以后,当我知道里面有大量的绘图时,和张焯院长提出要看这些绘图。从我研究的角度来说,已经把绘图从记录的手段转化为研究和解释的方法,有了性质的转移,让每个研究者可以在用文字表达结果的同时,也可以用图像表达成果,这样就能说清楚。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正如云冈石窟那样,如果绘的是一个三维佛像,绘图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写生的能力。能够同时表达质感和透视,这非常难。
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随着我们今天记录手段、储存手段和传播手段的发展,图像的研究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从长远观点来说,艺术史和考古学共同完成一些工作,现在看来已经到时候了。《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让我从这方面看到了可能性。

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原主任)
我们学界对《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可以说是翘首以盼。我知道考察云冈石窟的最大困难就是一些地方看不清楚,比如第6窟、第7窟等。这次《云冈石窟全集》能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些地方,解决了我这么多年来心中的遗憾。
20世纪80年代,宿白先生的文章,开启了中日最高水平学者关于云冈石窟的大讨论。讨论的诸多问题中,分期问题,尤其是第27窟,存在较大的分歧。年代分期需要用比较准确的图像来证实,这是我们当时非常想看的。但是因为地方太高了,在下面确实看不清楚,留下了很多遗憾。宿白先生在论证的过程中提出了“云冈模式”,这个概念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想了解清楚也必须借助清晰的图像。所以说这套书的出版把这些障碍都解决了。

余江宁(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
龙门石窟在历史上与云冈石窟就是兄弟关系。宿白先生当初在龙门石窟举办石窟考古培训班,要求大家做好石窟考古报告和基础资料的整理,这是石窟研究的首要问题,所以这次《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真正圆了宿先生的夙愿。
龙门石窟研究院非常荣幸有机会得到宿白先生的亲自指导,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心关怀。经历了13年,龙门石窟历史上首部考古报告《东山擂鼓台区》去年正式出版。现在《云冈石窟全集》又出版了,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会继续把龙门石窟的考古报告整理编写工作往下推进。龙门石窟基础资料的整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定要坚定文化自信,把石窟文化保护传承的任务不断推向前去。

谢继胜(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当我看到《云冈石窟全集》,确实很震撼。这套书出版之后,大家对云冈石窟造像的体系,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云冈石窟全集》把以往几次考查的遗迹做了全部的出版,是非常全面的,里面的记录会反映当时建造的技术,哪个地方钻了土,哪个地方打了铆等等。此外还发表了很多出土文物等,所有这些让我们看到整个石窟在发展过程中是什么样的情景。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
对于《云冈石窟全集》及其对今后研究的影响,我是很期待的。2015年,我有机会受张焯院长的邀请,带领学生去云冈石窟。张院长让我们利用早晨石窟开放之前的时间,登上脚手架近距离观察,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作品。试想,如果我们天天在洞窟里仰面观察,实际上跟北魏时期一直到辽金时期观众的观察角度是一样的。今天的研究者,不光是历史学者、考古学者或者艺术史学者,如果他们都还是在这样的层面观察,我觉得会忽略很多重要信息。当初开凿石窟的工匠们很有可能就是搭了脚手架,一点一点雕琢出来的,这种近距离就是那个时代石窟创造者的眼光和视角,这样的视角是艺术史研究应该具有的,《云冈石窟全集》无疑提供了这样的视角。

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文化遗产学系教授)
《云冈石窟全集》中不但有海量的照片,还有不少线描图,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绘图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你到底要什么信息?我们往往都会把考古报告编纂的最高理想看成是一个纯客观主义的、不加任何人工选择的东西,包括画风也是这样,不加任何修饰。但是在绘图的过程当中把三维的东西经过测量要变成一个平面的、二维的线图,其实就是个选择过程,你必须要选择。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因为《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我今天再次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以往大家在讲云冈的时候,日本人的研究一直压着我们,今天终于翻了身。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们虽然在批判日本,但是没有办法还是拿着日本的书在教学。我觉得云冈和敦煌比较来看,云冈被压得更为窒息,云冈受到的压力更大,云冈做起来比敦煌还要难,从这样的层面上看,这套书的意义非常重大。书中有了这么多清晰的图,让广大没有办法大面积近距离观察云冈石窟的学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为今后云冈石窟的研究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汪家明(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社长)
以往从来没有一套书会像《云冈石窟全集》这样,这么全面地把一个我们传统的艺术或传统文化遗迹全部地、多角度地表现出来,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一个做到这种程度的大项目,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如此完美,我认为对任何一个出版社来说都是一部镇社之宝。
现在的出版界,很多出版社也做一些大项目。相比之下,有些大项目并不值得那么大动干戈。而《云冈石窟全集》这个项目怎么做都不为过。从这个角度我相当佩服青岛出版社有这种魄力,这种眼光。作为同行,我也很羡慕青岛出版社能完成这个项目。作为一个读者,我还希望能有一套或一本小规模的,可以随便阅读的,又很好看的对云冈石窟的介绍的书,或者说把这个大项目再做一个普及版,我有这个盼望。

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这次很多学者提到了宿白先生,可以说中国石窟寺考古是宿先生一人开创的,他也培养了许多石窟寺考古的杰出人才,如樊锦诗先生和今天在座的李崇峰先生和杭侃先生等。但是,我们还要考虑的是今后做石窟寺考古怎么超越前人。《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表明,资料的发表已经走到学术界、研究界前面了,这部书提供了最新的、最完整的、最细致的材料,我们今后在培养石窟寺考古的人才方面能不能“为往圣继绝学”,这绝对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杭侃(山西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日本学者编著的《云冈石窟》是必读的,即便是北京大学,也只有在北大的图书馆可以看到,每次去能多看几册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由我们中国人编纂出版的《云冈石窟全集》,它涉及的新材料、新观点,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比如第20卷里有很多新的材料,希望做相关研究的学者能够尽快看到这套书,这样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让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