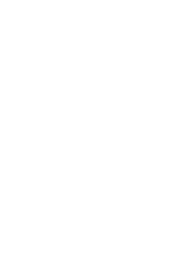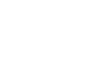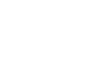2009年夏秋,我属于山西,属于大同,更属于云冈,就此与云冈结下了不解之缘。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城西16公里处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石窟坐北朝南,依山而建。东西绵延约1公里,除许多较小的佛龛以外,主要洞窟45个。兴建于公元五世纪中叶,北魏时代。现存造像51000余尊。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象生动感人,石窟气势宏伟,颇具“皇家风范”。造像数量之多,艺术之精湛,堪称当时世界美术雕刻最高水平。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同为我国三大佛教石窟艺术宝库,并先后被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也许人们不太相信这样一个事实,我在敦煌莫高窟从事文物摄影工作近30年,因公务事由,曾先后朝圣了克孜尔、库木吐拉、柏孜克里克、天梯山、马蹄寺、龙门、大足等知名大小石窟十余处,却从未到过大同,更未到过云冈石窟。这种愿望在心中形成了一个长久的期待。何时能去看看云冈石窟的艺术精品?似乎成为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有趣的是,世事真难预料。也许是天意,更应是佛缘,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圆了这个期待已久的梦。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我的事业与云冈石窟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那就是用我的相机镜头去描绘一个我心中的视觉云冈……
5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突然接到了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艺术大师冯骥才先生的电话,他说:“吴健,有个摄影项目你接不接?”我问:“是什么项目?”冯老师说:“想请你抽个时间拍云冈石窟,要出版两本大型精美的画册。”我一听喜出望外,不假思索地就说:“没问题,我非常愿意。”最后冯老师说:“计划在6月20日左右在大同召开编委会,你不光是摄影师,还是编委,到时,请你来参加会议。”6月21日,我参加了在山西大同召开的“新云冈计划——建造中国雕塑之都大同”会议,由于冯骥才先生大力举荐,我很荣幸地成为大同新云冈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云冈石窟艺术》画册的编委和总摄影。可以这样说,冯先生对我充满了信任。
那时,我对云冈石窟还是陌生的、好奇的。6月22日,我随与会代表们一起参观云冈石窟,当我第一眼看见云冈石窟时,我被云冈石窟的巨大气势和精湛的雕刻艺术震憾了,也茫然了,甚至目瞪口呆,几乎每个洞窟都很高大陡峭,好像仰首望断脖颈,也看不到建造雕刻在窟内高处的佛龛及造像。我惊叹,古代艺术工匠的鬼斧神工,太神奇了!我郁闷,如此高置的佛造像,如此狭窄的空间如何拍摄啊?太难了,太难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能用相机拍下来就很不错了,还谈什么角度?什么光影?什么镜头语言?此时,我有些担心和失望了,但我最担心的是有负冯骥才先生及诸君的厚望啊!会议结束后,我迫不及待地又进入石窟。在张焯院长和游客中心的赵昆雨精心安排下,我又仔仔细细一个一个窟地去看、去观察、去思索,毕竟在敦煌工作许多年了,对石窟的形制、内容、形式和艺术特征理解起来比较容易。再结合本专业——石窟摄影,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云冈石窟拍摄计划的雏形。此时的我,比起几天前第一次看到云冈石窟,心里平静了许多。开始考虑下一步如何具体实施这一庞大的摄影计划……
回到敦煌后,夜以继日用了近30天的时间,潜心查阅了有关云冈石窟的出版物,如日本著名摄影家羽馆易30年代拍摄的《云冈石窟》黑白摄影画册、《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上下两本画册,《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画册等大型出版物,仔细研究了每个画面的得与失,如角度的选择、光影的运用,色彩的处理、画面的布局等艺术视觉元素。同时,将敦煌石窟摄影的艺术特征和风格以及我对佛教美术的独特理念融合在了一起。于是,云冈石窟新的摄影方案开始成熟起来。
赴云冈拍摄工作得到了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纪新民书记、王旭东副院长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樊院长亲自在大同市人民政府公函上签字同意。随即准备必备的摄影设备、相关器材、感光器材等。我的摄影团队共4人,除我之外,其他3位均为20多岁的年轻人,有摄影助手丁小胜,计算机图像处理王江子和路育成。一切准备就绪。7月20日由敦煌出发,经河西、兰州、银川、包头、呼和浩特等地,7月22日到达云冈石窟。经过两天的休整和各项准备工作,7月24日下午,正式开始拍摄云冈石窟第1窟。由此,云冈石窟的摄影工作全面展开了。
云冈石窟,题材除主尊大佛、菩萨以外,最多的题材还有交脚弥勒菩萨、释迦多宝并坐佛、飞天、伎乐、装饰纹样等雕刻作品,数量之多,数不胜数。
石窟摄影,旨在立意,贵在创新,除宗教造像仪轨和特定的内涵以外,必须追求一个规则,一种秩序,一种神秘,一种形式美。根据石窟造像的特点,用镜头语言的表述比文字语言的表述更真切、更震撼、更感染人。它包含了更多难以口述的东西,只有用心才能感受到。我的云冈摄影工作一开始就要求自己紧紧围绕“新云冈计划”,突出一个“新”字,就是打破陈规,超越自我,大胆地去认知、感悟、探索、创新,这个过程还伴随着冒险和无畏,这是一种精神。
作为《云冈石窟艺术》画册主编的丁明夷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个“老云冈”。起初,当请他做主编时,丁先生不以为然,认为日本人拍了八年,出了十六本书,这些年又 出了很多书,有必要再出吗?能超越前者吗?带着满腹疑虑,他不情愿接这个差事。但是,当他听冯骥才先生说:“我把吴健从敦煌请来拍云冈石窟了。”丁先生即刻改变了主意,他欣然答应了,因为他认识我,也了解我对敦煌石窟的拍摄作品。在我拍到第7窟时,丁先生专门从北京来到云冈,要求看看我已拍的云冈石窟图片,当他看完几十幅作品后,老人家激动了,连连说“出彩了“,“比我想象的还要好”,“这就是新云冈“等赞叹话语。这不由令我想起,6月22日在大同开完编委会分手时,丁先生用一种非常恳切的目光对我说:“你肯定能拍好,要超过日本人。”我说:“丁先生,我不想超越任何人,我只能尽最大努力超越我自己。”因为在每个时期,每位摄影家都为云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将无数的艺术灵性、智慧和情感倾注在了石窟的每一角落,每一尊造像上,在许多方面,我应该向他们学习。虽说我在敦煌从事石窟摄影多年,但对云冈石窟还是陌生的,云冈与敦煌虽说都是大石窟遗址群,但存在很多的差异,相比之下,云冈的摄影难度要大得多,因为云冈石窟以雕塑而著称,是一个立体的佛国世界啊!云冈的摄影,冯先生在期待着,丁先生在期待着,其实我也在期待着,但就此时,我心里仍然忐忑不安。的确,压力太大了……
什么是云冈?何谓皇家风范?我总结为八个字:高大、华丽、气势、密集。
美的东西,是人人都喜欢去表现的。一般的甚至任何美感都没有的对象,你想拍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由于种种人为与客观原因,云冈石窟许多造像风化严重,残存不全。如佛塔、佛像、飞天、力士等,也许人们并不看好它们,但在我看来,如果运用好了摄影的语言,如疏与密、明与暗、大与小、冷与暖、虚与实等诸多手法。它们也就显灵了,这是一种难得的艺术“残缺美”啊。这种实例举不胜举。摄影艺术就是去寻找美、发现美、塑造美。为了拍好一个对象,必须去寻求每一个角度,甚至是人想不到的地方,也许这样仔细、反复寻找,你的角度才会是新颖的,视角上才能够创新。
云冈石窟不仅伟大,而且高大,几乎每个窟主尊造像都比较巨大。与乐山大佛、敦煌莫高窟第96窟、第130窟大佛相比,绝对高度则显得更加凸显。当我攀上9米高的脚手架时,举头望去,距窟内最高处的造像仍有7~8米,我仍在仰视。由于脚手架在石窟内搭建高度限制原因,只能“望佛兴叹”就此拍摄了。这样的情况,在云冈大型的洞窟拍摄时都有,常常遗憾……
云冈石窟的雕刻作品,具有浓郁的中西文化融合的气息,犍陀罗、秣陀罗两种艺术风格并存。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犍陀罗风格的雕刻作品,因为这种风格的雕刻作品,更加逼真、细腻、圆润、准确、亲切而感人。由于人们平日习惯的观赏角度或一些摄影师的拍摄角度太接近正视、仰视,使得许多浓郁“犍陀罗”风格的飞天变成了浅浮雕,若换个角度,其视角效果大相径庭,实际他们的躯体虽说是浅浮雕往往向后隐去,而其头部则近似圆雕,十分圆润,属于高浮雕作品,除优美的动感姿态外,面部表情也十分有趣。因此,摄影家的观察力是尤为重要的。主尊大佛在塑造时,身体及头部微微前倾,艺术工匠们在整体造型上有意加大了佛头的比例,使朝圣者瞻仰时与向下微倾的佛像目光容易对接,相互碰憧,产生一种人性化的共鸣。所以,拍摄大佛的正面,平视的角度往往是不理想的,是无法表达出佛像内在的、精神的、个性的、美感的一面。理想的角度还是符合人的瞻仰角度,但角度不能太仰,因为人的眼睛是双目、立体的、透视感较小,而照相机的镜头只是一只眼,二维的,特别是广角镜头,视角大透视也很大,故而拍摄角度比人们观赏角度往往要高出许多。其实,云冈石窟的许多佛像表情都在微笑,只是你找准角度,把握好用光,他们的内在生命力就显现出来了,给人一种格外的亲切感,菩萨的表情就更不用说了。
明窗拱门是云冈石窟每个洞窟的“门面”,更是一个洞窟真正意义上的“窗口”。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认为云冈石窟的明窗和拱门上的雕塑作品技艺水平是最高的,只是拱门太接近地面,风化残缺严重,大多数明窗上的雕刻作品基本保存完好,这个情况对我拍摄来说既有吸引力,也有挑战性,无论明窗有多高,有多陡,有多窄,我都力争攀上去逐一拍摄,但这里的角度太有限了,补光也太艰难了,因为摄影师的危险系数太高了(如第7窟、第8窟的明窗)。
云冈石窟的摄影,不仅是追求和解决一个高度、一个角度,还需要力求表现一种意境、一种氛围、一种内涵、一种韵味。
早期建造的昙曜五窟,主尊造像是以北魏帝王为蓝本和范本而建造的,这五尊大像造型夸大了身躯体魄,厚重雄健,人物造型比例适中,由于空间狭窄,佛的形体十分高大,自下仰去,高耸无比,佛身体尤显巨大,而头部则显得过小,尽管摄影机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拍摄到的佛像比例感觉仍不协调,这是由于在修建造像时,更多地考虑了政治、民族、宗教等因素,并没有顾忌到日后人们的鉴赏目的。在塑造时,佛像过于挺拔,没有加大头部比例和身枢的前倾角度,好像与人的目光无法对接。因此,这几尊佛像除高大以外,艺术造诣似乎不是太高,显得不甚优美。而第20窟的坐佛,之所以它能成为云冈石窟的象征、代表作,因为它已是露天大佛,人们可以在一定的距离内去欣赏,从而缩小了视觉上的透视和差异。如果这个洞窟南壁不坍塌,佛像仍在洞窟中,那就是另一种效果了。
在云冈,最苦恼的拍摄对象是包了泥的佛像,因为包了泥巴又刷白的雕塑已失去了原始造像的棱角和线条,尤其是多年的煤灰沉积在雕塑身上、头上、脸上,像苔藓一样牢固,看上去雕塑很“脏”,无论怎样拍,直观效果都不理想,遗憾之至!
在云冈拍摄期间,我不仅仅是一名摄影师,也是一位清洁工。几乎每个洞窟的雕像身上都覆盖和堆积了多年尘土,有时厚达5~6米。这些尘土使精美的雕刻作品“蒙尘”,让他们失去了色彩、光泽线条和往日的辉煌,如同出土文物一般。如果你像游人一样匆匆走过,或从上往下看似乎感觉有些不适,因为这些尘土躲避在雕像的上面,而从摄影的角度来看,就大煞风景了,你的创作激情也都会大打折扣了……
为了能拍好一幅比较理想的雕塑作品,每次在拍摄前或拍摄过程中,都要对被摄雕像进行除尘。刹那间,洞窟内弥漫尘土煤灰。出了洞窟再看我们就像刚从煤窑里出来的一样,身上、脸上又是白的,又是黑的,可大伙都风趣地说这是北魏的……疲惫的身躯倚靠在窟前的立柱下,或席地而坐在窟前的台阶上,浑身尘土,颜面蒙灰,极其狼狈不堪。有好奇的游客从身边走过,投来一种诧异鄙视的目光,有人对曰:“唉,这是民工在维修吧?不对,是打扫卫生的。”
从云冈驻地到窟区,途经一段崖体,上面布满了小龛,但都已千疮百孔,里面的造像早已风化雨蚀,面目全非了,留下的只可辨认出一具具的残骸躯体。每过这段路时,似乎这些残骸遗存佛像在目送我远去。这些残窟残像,与精彩的石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这些风化无几的残存佛龛映入眼帘时,我内心被刺痛,在流血。一天,突降倾盆大雨,还夹杂着豆大的冰雹,许多游客本能般地急速躲在窟前廊檐下,我与他们一起滞留在这里,雨越下越大,像瀑布一般。突然,我的目光穿梭了飞流的水帘,在幽暗的残窟中,再次依稀看到了龛内的佛像残骸,似乎它们向人们倾诉着什么,是在哭泣吗?对,它们在流泪,这场大雨就是它们的眼泪呀。此时的我,心情更加沉重,一种责任感涌上心头。为保护好、拍摄好世界遗产——云冈石窟珍贵的佛教雕刻艺术品,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值得!
每日无数次攀登高9米多的三角铁架,手指、脚趾、膝关节酸痛不已,一旦坐下小憩,想再站起来都不太容易,浑身像组装的一样,只有依靠外力的搀扶,才能勉强站立起来。然而,咬咬牙又走向了铁脚手架子。
常言道“闻鸡起舞,而我们则是听见了景区内树上的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噢,天亮了,拍摄工作方才结束,收工回去以后可以入睡了。每天如此。
摄影人总喜欢用黑白照片来表现历史,因为黑白的特殊影调可以推远历史时空。每天从洞窟结束拍摄回到宿舍,检查完当天拍摄的图片后,将喜欢的彩色图像在电脑屏幕上变成黑白片,可以感受到内容以外的东西,如影调、层次、光线、时空感,或者什么?这一通变来变去,由彩色到黑白,再由黑白到彩色,你一句,他一句地还在评析,这时,麻雀又叫了,天又亮了。
在云冈夏季的夜间拍摄最苦恼的就是被蚊虫叮咬了。当灯光一打开,成千上万的飞蛾扑向了灯和我们,飞蛾永远是愚昧的,瞬间扑灯自焚,而蚊子却悄然叮住了我外露的肌体,防不胜防。十几天来,我们的年轻人江子喜欢卷起裤脚干活,结果上下被咬了个透,密密麻麻,真是体无完肤了。再看我,两只外露的手臂,几乎被蚊虫咬了个遍,一个个小红疙瘩布满了双臂。听云冈的同志说这是一种又黑又小的本地蚊子,十分厉害,且毒性很大,被咬之后几天内是不会好的,怪不得我的两只胳膊一摸真像“狼牙棒”似的,疼痒难忍……
江子和小路是做计算机工作的,但在此次的云冈拍摄工作中,我教会了他们如何布光,反光。从此,他们担负了洞窟最高处打灯布光的工作。小胜戏称他们为灯爷。“灯爷”这项工作十分重要,是摄影工作的基础,有时他们站在高低不平、空间狭窄,高达10多米的明窗上面,按照我的要求,将3米长的灯杆高高举起,纹丝不动,一举就是2~3小时。而每当看到拍摄的照片时,他们似乎早已忘却了当时布光时的艰辛和险情了。小胜是摄影助手,高大有力,憨厚诚实,这次随我来云冈拍摄对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实践机会,每天像上足的发条忙个不停,安装机器、搬运器材、洞内除尘,眼中的确有“活”。每次我问他累不累,小胜憨笑一下,说不累,回头睡一觉就好了。
摄影工作进行到第8窟时,大家因身体透支都已经深感疲惫了,三个年轻人时常无精打采,突然间,好像失去了以往的活力。的确,掐指算来,已在云冈工作二十几天了,夜以继日,连轴转的工作方式,肯定会使每一个人都吃不消的,其实我也是在硬撑着呢。因为进入“五华窟”,几乎属于露天石窟,白天太阳会直射洞窟,形成明暗强烈的反差对比,加上正值旅游高峰,游客的涌入与干扰,工作时间只能安排在每天下午6点以后进行。自此,几乎一干就到次日凌晨4~5点,通常回到市内酒店,天已亮了。但即便如此,每个人仍不能休息,稍加小憩,小路就开始将每天拍摄的所有数字图像转入电脑并进行存储。同时,我也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做,就是要把当天所拍的石窟内容凭脑中回忆记录下来,每天如此,无论多晚多累都需坚持,这也是常年养成的习惯。数据存储完以后,小路将电脑搬入我的房间 ,小胜、江子和我四人又开始一幅一幅地认真观看,当看到精彩的图片时,大家兴奋起来,一点睡意也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我非常感动,也很欣赏这三位敬业的年轻人,我半开玩笑地说90分钟的足球赛,球员最艰难的是第65~75分钟,如果能咬牙坚持,能及时把体力不支的状态调整合适,就可以等待最终胜利的哨声了,而我们现在的摄影工作如同一场正在比赛中的足球,时段已到了第70分钟,大家都己疲惫不堪,体力不支,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更没有替补,而且必须要赢下这场球,只有咬牙坚持,很快就能听到终场胜利的哨声。说到这里,三位年轻人表示理解和赞同。
为了做好云冈的摄影工作,云冈石窟研究院张焯院长专门安排了八个民工协助,其中马师傅等五人白天在洞窟外围搭通往明窗的钢管脚手架,以范谦师博为首的三位随我的团队做摄影协助工作,如搬设备、接电线、抬三角铁架子、搭木板、递东西等,尽管只有三个人,但阵容老在变。只有老范一人没变,其他两人都觉得这活太累,工作时间太长,挣钱太少都不干了。但是,时间过了十余天拍到第6窟时,老范被我感动了。确切地说,被我对云冈石窟一片挚爱感动了,他看到我攀高爬低,拼命不停地忘我工作,老范深情地对我说:“吴老师,您辛苦了,太累了,你在为大同人民做事情,你是在积功德,不管别人干不干,不管挣钱多少,我老范都要陪吴老师把摄影工作干完!”质朴的话语,真情的流露,我的心热了。老范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人,一个真实的大同人!后来大家互相离不开了,一旦有事年轻人都喊“范师傅”,因为老范最勤快、最干练。我们都会永远记住你,范谦师博!
拍摄第15窟的那个夜晚,天降细雨,包括三位工人师博一共7人,都挤进了这个洞窟。该窟雕刻的千佛密密麻麻布满了四壁,因而有千佛窟之称。在东西两壁下方各有佛龛,只是尘土堆积太厚,几乎无法辨认雕像面目。于是,开始清扫佛像身上的灰尘,半小时以后尘埃落定,可以拍摄了。当灯光投向西壁佛龛时,龛楣上的几个小小的雕刻飞天好像动了起来,姿态非常优美,连老范都在赞叹:“吴老师您的灯一照,这些飞天看起来真好!”我说是的,范师博也说大部分人到了云冈石窟,只关注第20窟大佛的高大,第6窟的华丽造像等知名作品,而这些小的造像往往会被人遗忘和冷落,但他们是石窟中重要的内容和组成部分,我应该把这些题材拍好!也许云冈的雕塑太多太多了,选入镜头中的我认为就是最好的。我又对老范说:“范师博,云冈石窟是你们大同的骄傲呀!”老范连连说:“是,是,是。”为了拍摄第15窟的形制,需要从洞窟外补光,小胜、江子分别在细雨中支起一盏灯,他们怕灯具被雨水淋坏了,便各自拿了一块纸板遮在了灯具上方,而他们却悄然伫立在雨中,等拍完一组镜头以后,他俩浑身都湿透了。
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有多少艺术匠师们营造的佛教石窟艺术,创造了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奇迹,令后人享用不尽。
终干拍摄到石窟西部“唱晚区”了,心情十分沉重。拍摄重点工作是去寻找窟中美的身影,但十分困难,并非西区石窟不好,而是风化损坏太严重了,有个别好的雕刻作品,也是凤毛麟角,我力求我的作品不要“唱晚”,极力用摄影镜头语言去寻找,再现西区往日的辉煌。尽管有的雕刻已残缺不全,但也有相对完整的雕刻局部艺术造诣很高,触动了我的心灵的雕刻,我都会认真、仔细地去拍好它,毕竟残缺美也是美呀!
第39窟,内有五层方塔,是该窟的主体建筑。当拍完这座塔柱时,我的云冈拍摄工作就基本结束了,非常有趣的是7月24日我拍云冈的第1张照片是第1窟的佛塔,而8月29日我拍的云冈最后一张照片仍然是佛塔,难道这是巧合吗?常人道:修塔造像功德无量,那么我这个拍塔之人,是不是多少也有点功德呢?
云冈石窟的拍摄工作终于结束了。仅仅一个月的摄影时间,不可思议,简直是一个神话,但我愿意做一个创造神话的人。
也许有的读者看到我拍的云冈石窟摄影作品时,会提出一些异议,如这个角度再远一点,再高一些,再偏一点,再正一点,或再……一点,作为作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殊不知往往为了拍好,甚至能拍到一尊佛像,在10多米的高处上演杂技,一只脚站在铁架上,另一只脚及半个身子都悬空了,稍不留神就有掉下去的危险。一句话,尽力了,一切都达到了极限:角度、景别、高度、镜头与我。可是拍摄云冈石窟除对石窟艺术的认知、精湛的技艺、创作的激情以外,还必须富有冒险精神,这也是非常人可为的。这不是危言耸听,在拍摄工作期间,几乎每天都会玩杂技,有时像蜘蛛侠一样,拍完可心图片以后往往隐隐感到后怕。正如日本人长广敏雄在他的《云冈日记》中写道“当年他的工作组最重要的就是摄影工作”。至今,我真的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了。
“灵岩之美,千古绝唱。”云冈的摄影工作虽说结束了,但这段经历为我整个人生增添了浓重的一笔,有许多的认知,许多的收获,许多的惊奇,许多的遗憾,更有许多的感悟。
除了感悟,就是感谢。首先非常感谢冯骥才先生的举荐,使我有生之年拍摄著名的云冈石窟,使自己的事业之路可以拓展和延伸;感谢云冈石窟研究院张悼院长等领导及朋友,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予我们细致入微的关心和帮助;感谢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纪新民书记、王旭东副院长,以及数字中心同事的帮助与支持。总之,要感谢的人还很多很多。在此,一并致谢。
8月30日离开云冈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临走时,我专门又去第19窟、第18窟、第16窟、第20窟,仿佛在话别。看到一尊尊熟悉的佛像备感亲切,转身离去时,能隐隐感觉到它们的目光集中注视在我远去的背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