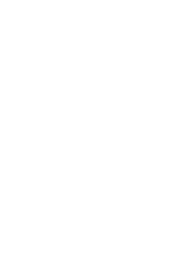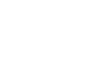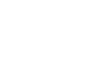位于今山西大同市西十六公里武州山麓的云冈石窟,自北魏创建以来,历经一千五百余年的沧桑,至今遗迹斑然。幸运地保留了五十三个洞窟,五万余身石雕佛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大文化宝库。
云冈石窟有它的极盛时期,那就是北魏当年建成时,“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⑴是鲜卑人在他们的京郊创建的一大壮观。也有它的衰颓时期,那就是隋唐时,“荒郊处处生荆棘,塞飚动地牧马嘶。君不见,当初魏都行(乐)处,只今空有野风吹。”⑵这是由于突厥人侵犯边塞,这里是兵戎相见的古战场。又有它的中兴时期,那就是辽金时,“峰峦后拥,龛窒前开。……三十二瑞相,巍乎当阳;千百亿化身,森然在目。烟霞供室座之色,日月助玉毫之辉。神龙夭矫以飞动,灵兽雍容而助武。色楯连延,则天皇弥勒之宫;层檐竦峙,则地通多宝之塔。”⑶这是契丹人、女真人两次对云冈木构寺庙的重修装饰,它不仅恢复旧观,而且辉煌一时。还有它长期冷落的时期,那就是元明清时,蒙古人铁马金戈不顾这事,朱家王朝花天酒地不管这事,明清交替之际,“是非莫辨,玉石俱焚。楚猿祸林,城火殃鱼。……(大同)为狐鬼之场者五阅春秋。”⑷这里遭受闯军的战火,姜瓖的降叛,满清的屠城,云冈备受兵燹。满人在安定之后虽亦稍加修葺,然已面目全非,与当年盛况不可同日而语了。有清一代云冈沉默于紫塞边陲,鲜为人知达二百余年。
本世纪初,法国人沙畹(E•Chavannes)、日本人伊东忠太郎等,著文、摄影公诸于世,才又赫然引人注目。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几代学者如:掾本善隆、小野玄妙、关野贞、常盘大定、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广为撰文发论,大肆宣扬。议论云冈者蔚然兴起,涉及:艺术、佛教、考古、历史以至民族,各执一端,众说纷呈。中国著名学者如:陈垣、梁思成、刘慧达、阎文儒、周一良、宿白等,自三十年代以来,也有许多论著公诸于世,提出许多卓有见识之论。为研究云冈奠定了基础。
随着旅游风气的兴起,云冈石窟已成为一处热点。游人们愿意知道云冈的来龙去脉,更愿知道它的价值所在。
作为世界性的一大文化宝库,它的文化价值何在?作为世界性的一大艺术宝库,它的艺术价值又何在?作为北魏王朝的历史博物馆,它的历史价值何在?作为佛教一大名胜,它的宗教价值何在?作为旅游观赏的古迹,它的美学价值又何在?这些问题前人尚未充分论述。若从“文化”这个大视角、大背景下去鸟瞰云冈石窟,并分门别类地剖析其价值内涵,对云冈的研究可能会深入一层。本文试从文化价值的讨论着手。
一、石窟文化
“石窟文化”是我在1989年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撰搞时提出的一章专论。这个命题是否科学?能否成立?尚未充分讨论。这里从肯定的角度作一点探讨。
“文化”(Culture),自身的概念就比较庞杂,名目也相当纷繁。加上我国近来的“文化热”,各种文化名称纷至沓来,使文化概念有流于庸俗的倾向。此际提出“石窟文化”亦难避凑热闹之嫌。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石窟,或从石窟的现象谈文化,却倍感清新,别有洞天。
我对众多的文化概念,从返本求真的角度撷取了中国儒家学说中的一个含糊观念,即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⑸将这一不太引人注意的文化观念作为文化的基本定义。因为“质”与“文”确系产生文化现象的根本。它二者间的交互关系是人类与其他动物分离后率先发生的现象。当人类从初始的朦胧中觉醒过来,第一次使用遮羞蔽体之物开始,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地用一点身外之物——那怕是一片树叶,文饰了自我。文化现象也就发生了。随着人类在生存竞争中日益扩大领域,为对抗自然需用多种物质,为应付社会需要各种精神。因此,人自身固有的“质”,必然要以身外的“文”去不断装饰,不断美化。以后人类从维护生存、美化生活、健全思想出发,创造了无尽的物质文饰(文化)和精神文饰(文化)。一个个文明社会形成了,装饰与美化人本的文化日益发展,于是门类繁多,内容广博,五彩缤纷的灿烂文化与日俱增。但这些现象的宗旨,总不出:文饰人本。如果承认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之物,那么我说文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完善人本自我;文化的作用就是对人本质的文饰;文化的动力是人类为生存而需要物质,为理想而需要精神;文化的效果是社会的文明进化。
如果把“石窟”这种现象,也从某些人类(某民族)为了完善自我;为了将其自身之质文饰成为神佛;是一种精神升华的物质表现形式;是一项文明的标志;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现象。那么“石窟文化”可以确立。事实上至今遗存的许多石窟遗迹,正展示着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风采。
综合分析石窟文化的表现形式,约可归纳出七种特征:
第一特征:石窟特征
石窟,是石窟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首要特征。此“石窟”有着特定的含义。它不同于古人穴居野处所用的岩洞或洞穴,也不同于供人观赏的自然溶洞。石窟的目的是人们为了满足一种精神的需求,即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而创设的一种宗教活动场所。它不是人们的物质需要,但它是纯属精神需要人为地开凿而为其目的服务者。
石窟的表现形式是:佛教信徒为实行其宗教活动,或为坐禅修行、或为供佛礼拜、或为宏扬佛法等,选择风光秀丽,山水相连,僻静幽深的灵岩圣地,于山崖岩壁,开洞窟,造佛像(有石雕、有泥塑、有壁绘),行佛事。以企祈福往生极乐世界。此中凝聚的是:佛教信徒及社会人士的精神寄托、精神向往,精神享受。故而表现为一种精神世界的文化现象。而与那种为生存、生活的物质需求的“洞穴文化”判然区分了。
第二特征:佛教特征
人们按照自己的某种意愿开凿石窟并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是佛教创立的。以后的发展也是按照佛教的宗教要求发展的。终极成果也仍然是佛教的文化现象。
佛教开凿石窟无非是两种功能,一种是坐禅,一种是供佛。坐禅是印度僧人的传统,传入中国后被中国僧人广泛接受,故坐禅窟在石窟中占一定的比重,但它还不是石窟文化的代表。能代表石窟文化的是供佛窟,这与寺庙供佛是同一目标下的两种文化形式,石窟供佛有它的独特的文化表现。
佛教在供佛问题上有过长期的争议,起初只是以保存佛的牙、发、爪、舍利,并为之建塔贮存以示纪念。对佛陀画影、塑形不甚注意甚至反对。经过几百年,随着希腊文化的入侵印度,造像观念有所改变。佛像出现后,先是兴建伽蓝寺庙作殿堂式的供养,由于寺庙的局限性太大,才又回归山林,创造了石窟供佛。
佛教在石窟供佛上创建很多,借着石窟的条件扩大了供佛的内容,保存了古老的佛像。在供佛内容上,除以释迦牟尼为主线外,又开辟弥勒佛一条辅线,又把三世诸佛、十方诸佛纳入石窟,使佛教的多佛信仰得以充分发挥,至于菩萨、罗汉、弟子等无不赋予充分表示的场所。此外又扩展出佛本生、佛本行、经变故事等内容丰富的供佛题材,使石窟文化有了十分充实的内容。
至于中国石窟在佛教内容以外还有道教的和儒释道三教并存的现象,这些只是在佛教石窟基础上的摹仿与深化,仅是支流,不能代表石窟文化。
第三特征:民族特征
中国石窟文化的缔造者并不是汉族,而是西北和北方的古代少数民族,所以保留在石窟中的民族色彩非常浓郁。
沿着古丝绸之路,古疏勒人、龟兹人、高昌人、羌人率先在西北开凿石窟,接着鲜卑人在北方、中原继续开凿。他们把各自民族的心态、感情、信仰、习尚等传统文化,大量寄寓于石窟中。
在表现民族心态和民族感情上,集中表现在把人格化了的佛作了民族形象的处理,佛的三十二相反而居于次要地位。中国西部石窟无不留下当地民族的典型形象,他们把人格化的佛,按照本民族的形状去寄托感情。
在民族信仰和民族习尚方面也有非常细腻的表现。他们在塑造佛教神佛以外,还要按照佛教格式塑造他们民族所崇拜的神仙、鬼怪。还借石窟描述他的日常生活习俗。
就这样把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典范,民族精神,渗透到石窟文化中。
第四特征:民俗特征
与民族特征有着共同基础的民俗风情,在民间工匠的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留在石窟中,这些作品往往冲破佛教的束缚,极富有生活气息,而且生动活泼。
表现突出的是对佛教极乐世界的描绘,那无限美好的天堂净土,无非是当地人们理想的生活世界。在这里他们还把深入民心的纲常伦理观念、民众道德观念、日常生活状况、习用的器具用品及民众的审美观念等,都溶汇在石窟文化之中。
第五特征:艺术特征
创立石窟文化的古印度,在创造伊始就吸取了古希腊与古波斯的艺术,结合其印度本土文化创造出一种风格独特的旃陀罗艺术、秣菟罗艺术。传到中国,则先受古龟兹文化的薰染而出现克孜尔风格;又受五凉三秦文化的浸润而出现敦煌风格;再受鲜卑政权的强压而出现云冈风格,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出现龙门风格,当遍及中国各地区之后,各地的文化新血液无不输入到石窟艺术中去,而各地、各时的石窟又都以千姿百态的艺术形式,表达着当地、当时的文化水准。
石窟艺术,是一个完整的而且也是特殊的文化形式。它自身具有着超越现实的典型概括性,因而是浪漫的;同时它又是取材于生活的原型和社会实际,因而又是现实的。它在表现宗教内容时,既用浪漫的抽象去表现宗教的理想,又用现实的具象去表现宗教的仪轨。所以石窟艺术既是宗教艺术,也是社会艺术。它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放射着文化的光芒。
石窟艺术具体表现在:洞窟的形制、壁画、泥塑、石胎泥塑、石雕、摩崖大像,以及窟前的木构建筑(不过木构建筑不应包含在石窟文化中)。对这些具体形式的研究已有很大的成果。但在类比与确定某一个具体的个性上尚欠火候。往往一句“犍陀罗风格”就把一组石窟与千百造像遮盖了。到底那一点是犍陀罗的?那一点又不是犍陀罗的?那些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或叠加?都说得似是而非。对此,须有微观分析的进展。
第六特征:地理特征
石窟文化受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双重影响,而地理条件又决定了石窟与造像的形式。
就自然地理而言:各地的地理环境和地质结构成为石窟形式的先决条件。就中国而论,新疆克孜尔、敦煌莫高窟地处戈壁沙漠,窟内宜塑、宜绘;陇上麦积山地处黄土高原,窟内尤宜泥塑;塞北云冈地处侏罗纪砂岩地带,窟内宜雕琢;中原龙门地处华岗岩带,尤宜雕琢等等,自然条件决定了石窟的或雕、或塑、或绘的选择。
就人文地理而言:西域与西北地区在十六国时期,有一段相对稳定和政治环境,五凉三秦进行了辐度较大的民族文化融合,同时接受了丝绸之路传来的西方文化,形成了五凉三秦的先进文化体系,佛教文化是它们重要的选择,石窟文化就应运而产生了。塞北高原由于鲜卑政权对文化兼容并蓄的政策,在其都城中心出现了一个文化高峰小区,西部诸民族所选择的佛教文化被他们应用并推广了。中原地区在少数民族第一次统治后,少数民族的文化又熔铸于汉文化中,石窟文化就成为融合结晶之一。由人文地理的先导而敷衍出石窟文化体的分布。
第七特征:时代特征
中国石窟自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至明清之季,代有建造,而各个时代的石窟与造像亦无不具备显著的时代痕迹。尽管主题与内容差异不甚明显.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工艺、时代的需要,则有明显的区别。所以时代又是石窟文化的一大特征。
敦煌石窟延续时间最长,跨越了几个朝代,从而也汇萃了各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艺术精华。故而可以说,敦煌石窟是纪录西北文化的历史长卷。
云冈石窟工程期间最短,仅北魏一朝。所以集中表现了北魏王朝的精神状态和民族情调。故而可以说,云冈石窟是北魏鲜卑统治者的历史专篇。
龙门石窟极盛于盛唐时代.丽唐朝又是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如果把唐代文化归结于大量融合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结果,那么龙门石窟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结晶。
大足石刻则把宋代的溶儒、道、佛于一炉的时代学术风潮,贯注于石窟文化之中。
石窟文化.从印度开创的半天然、半人工的坐禅窟,发展到纯人工雕凿的供佛窟,再发展到中国式的像征帝王、用石窟寄托精神。把佛、菩萨人格化、社会化、把佛经故事化、把弥勒佛世俗化——大肚弥勒的出现,等等发展过程,都饱含着时代的精神与审美。按时代的进程可以理出一个石窟的发展轨迹,而在轨迹的每一个点上,又表现着浓郁的时代气息。这就是石窟文化时代特征的所在。
在上述七项特征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对石窟影响很大,那就是政治因素。几乎所有的石窟工程都与当时、当地的政权息息相关,不少石窟中的佛像是象征着帝王的,也有直接把人间统治者纳入石窟的内容者.如“帝后礼佛图”。一部石窟文化兴衰史,可以说是各代各地政策方针演变史的缩影。那么政治因素可不可以成为石窟文化的一个特征?我以为不可。因为政治因素只能作为石窟文化的背景,它不是石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不是石窟的实体部分,对政治无直接表现.所以政治不能成为石窟的文化特征。
二、石窟文化在云冈的体现
金代曹衍在撰写《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文中有一段评论:“然而,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与天地而同久。虑远而功大矣。与夫范金、合土、绘丝者,岂可同日而语哉!”云冈石窟之所以创造出这番石破天惊之举,有如此的宏伟规模,有这般的豪迈气派,有从洞窟到佛身以至装饰器物全部石雕化的创建,有能力集中于一个朝代完成全部工程,等等,都和曹衍所说的文化意识分不开。鲜卑人能产生这样的文化意识,是有其族属的文化传统、历史渊源和政治背景的。
拓跋鲜卑,祖居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徒,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⑹是一派典型的原始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从大兴安岭遗存的嘎仙洞石室,可以窥视到他们早期的文化基础。以后经过几世几代人的南下迁徙,越过“九难八阻”的地理艰险,吸取北方诸民族的各种文化,到在拓跋珪在中国北方建立政权时,鲜卑人已经融合了许多北方文化,极大地提高了他们民族文化的水准,并对来自西域的外来文化也有所接触。拓跋珪率先接受了佛教文化,尽管当时对佛教理解不深,仅以“胡神”看待佛,但对沙门法果却优礼有加,法果也打破沙门不礼拜皇帝和教规,将皇帝视作“当今如来”,不仅礼拜,且得到信任。借此,法果于天兴元年(398年)在京城内外创建了弘扬佛教的三大基地,即五级佛图,耆阁崛山,须弥山殿。此中的耆阁崛山,有可能就是京城西武州山的那个天然岩洞(今云冈第三窟),于是武州山也就成了灵山圣地(后称灵岩)。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数次祈祷于武州山并定为“常祀”,该是与此有关。从此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的道教文化、儒家文化,在鲜卑政权中鼎足而三地占据了一席之地。
第三代皇帝太武帝起初对佛教也信仰并支持,还滋生出一股实力很强的寺院经济。后来盖吴起义把西安的大寺院牵扯进去,或者西安的寺院经济正是盖吴的后盾。太武于平息盖吴中发现了西安寺院经济的实力和武器装备,一场灭佛的政治方针就确定了。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大灭法”实施了。尽管监国太子反对并加以保护,但土木宫塔,胡神形像的泥人、铜人,尽皆击破焚烧。佛教文化与政治发生了冲突。七年以后,第四代皇帝文成帝即位,立即“复法”,而且来势很猛,出现“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复矣”⑺的局面。这是一种逆反意识驱使,也是一个政治变革的反映。灭法时破坏最重的是土木宫塔,复法时则以石窟对之;灭法时指罪的是供养泥人、铜人者,复法时则以石佛对之,一灭一复.变本加厉。而佛教文化则在寺庙文化的基础上开创了石窟文化。石窟,虽有西域石窟(含阿旃陀、巴米扬等外国石窟)、河西石窟(指十六国时期的一些小型开凿)等可资借鉴,但创造如此宏伟规模与气势的石窟群,在中国尚属首例。其伟大意义则在于使中国的石窟文化开始进入成熟期,也可以说开始有了完善的第一组石窟文化体。它是中国石窟文化的一座里程碑。
由此归纳云冈石窟文化的表现,在石窟文化的七项特征中是完备的。
1、使石窟特征进入全石化的完善阶段
早期五凉三秦时在河西开凿的一些石窟,尚属开石窟而塑泥像、绘彩壁.可以说是石窟文化的不完整阶段。云冈石窟则既开石窟又凿石像,使石窟文化步入全石化的完整阶段。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尽管有些自然条件的便利,但文化意识的作用更为主导。鲜卑人肯于支持这种全石化的工程,远的有他们祖居石室的传统文化流衍,近的则有铸成“与天地而同久”的创立永世之功的逆反意识,所以才造就了这一文化创举。
石窟特征的主题是精神需求。云冈石窟在这一点上表现尤其突出。如果说早期河西石窟多坐禅窟,而坐禅窟又多少含有一些生活或生存需要的话,那么云冈石窟这种大型的供佛窟则几乎没有坐禅的条件,只能作供佛、礼佛、绕佛之用,再就是为帝王、父祖祈求冥福的意念寄托,使它和属于生活、生存需要的物质性的洞穴彻底分离,而成为纯粹的精神需要的石窟。这样就把石窟特征的含义更为完整地体现出来。从而使石窟文化更充实饱满。
云冈从第一窟到第二十窟是主体,都属于皇家气派的大洞窟、大佛像。从昙曜“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⑻开始,造大石窟的文化观念就落脚于为皇帝祈福,借供佛以象征帝王,借佛像以表现鲜卑人的顶天立地、盖世无双的气度。把人们的精神寄托、精神慰藉,引导到一个新的高度。与那种“凿仙窟以居禅” ⑼的观念已不可同日而语。县曜五窟凿作穹窿顶,平面为马蹄形,正是把鲜卑人曾经居住过的洞穴、氊房引入到石窟文化中的写实,这又是鲜明的文化承传与文化发展的痕迹。随后进一步发展,则出现作四方平顶、呈方形平面的窟制,且又分出内室与外室。这又是把内地房室建筑文化引入到石窟文化中的写实。再有一种在窟的中央立四方塔柱,平面作回形的窟制,并且雕饰丰富,这正是外来石窟文化的造形引进,但又有所创新。云冈石窟以这样三种窟形组成其主体,充分体现着它的石窟文化观念在于精神的向往。至于西部从第二十一窟到第五十三窟,虽属于一些民间工程,且偶而也有几个可供坐禅用的小洞窟,但其主导的文化倾向仍属于云冈主导观念的范畴,规模虽小,气度不凡,对石窟特征的表现依然是充分的。
2、使佛教特征明显地社会化
从石窟为坐禅,到坐禅与观佛并举,再到纯为供佛,这几个发展变化阶段使窟内的佛像布局也发生变化。再加入社会背景与政治因素,石窟文化中的佛教特征则愈趋纷繁。
北魏自法果和尚提倡“皇帝即当今如来”之后,已经萌发了佛与皇帝神人合一的观念。经过太武灭法的挫折,文成复法伊始便在兴安元年(452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⑽旋即又于兴光元年(454年)“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⑾把神人合一的观念推上高峰,而且毫不掩饰。和平初(约460年)昙曜奏请“开凿五所,镌建佛像各一”时,正当这种观念的高潮期,五窟五像不能不与帝王合一,这样佛教五像的选择,就得突破前期造像多为释迦、弥勒的范围而别开生面。
自昙曜在“昙曜五窟”造五方佛开始,将佛教供佛的领域拓宽了。从佛教空间观念所设的方位于佛中,五方佛、四方佛、十方佛等应运而被选择;从佛教时间观念所设的过去、现在、未来千佛中,过去七佛、现在释迦、未来弥勒等三世诸佛也在选择之列;从净土观念出发,东方琉璃净土的药师佛、西方极乐净土的阿弥陀佛、天宫兜率净土的弥勒菩萨等亦多被选择;从法华、华严经义又引出文殊、普贤、观音、势至等诸菩萨的选择;尤为突出的是依《妙法莲花经》所记释迦、多宝二佛并坐讲法像,在云冈诸窟多次出现。如此种种不但把佛教供佛的范围扩大使佛教特征更加浓郁,而且以众多的佛、菩萨巧妙地作为诸帝王、众贵族的象征。把神人合一的政治要求创造的更加完美,也把石窟文化导入时、空无限的领域。
如此,云冈石窟之专为供佛而开凿的佛教特征则兼具二义:一者使佛教的多神论得以充分发挥,使诸佛菩萨各得供养场所;二者把佛教从飘渺的虚幻中引回到现实的社会里。神人合一的宗旨既落实了佛教,又宏扬了佛教。云冈石窟也许是有此基调,所以能把佛教的诸佛、菩萨、罗汉、弟子、供养人等的选择纯佛教化,所有造像必有佛教的张本。这就不同于敦煌莫高窟等画像中出现羼入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仙,如东王公、西王母、雷公、伏羲、女娲等的情形。云冈的这一纯佛化的创举,把石窟文化的佛教主体作了巩固与突出。它也对以后的石窟造像的主题选择影响深远。如龙门‘、响堂山、巩县等石窟就不离佛谱。大约到宋元当石窟文化已转入衰退时期,才把这个模式打破,出现儒、道、释并存的、非佛教的石窟,但那已经不能代表石窟文化了。
3、使民族特征表现在民族心态上
鲜卑人以一个文化基础薄弱的民族,在取得了政权,统治了大半个中国,臣服了文化优于自己的汉民族后,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卑感始终交织在一起,心态是不平衡的。崔浩碑刻《国书》,触及到他们的短处,招致杀身、诛族之祸。昙曜造石窟就不得不借鉴这前车不远的教训。昙曜与众造窟者注意到这一点。
首先以佛像的雄伟高大来象征拓跋帝王的威严尊贵,树立了鲜卑人民族形象的自豪感,无论是顶天立地的立像,还是巍然危坐的坐像,或是端庄慈祥的法像,都具有一种振摄人心的威力,表现出一种举世无双的气魄,他们似向人世间作狮子吼般的大声宣布:我们鲜卑人就是如此雄伟,如此高大,我们是优秀的种族,我们要主宰世界。
其次表达了鲜卑民族在文化融合中的抉择与偏爱,并把游牧民族的独有风情作了细致的刻划。如第十二窟,就把一堂庄严肃穆的礼佛庆典鲜卑化了。它所采用的乐器既不是印度佛教传统的宗教乐器,也不是汉族宗庙祭祀或隆重庆典所用的“雅乐”,而是大胆地采用了游牧民族惯用的。短歌箫铙”类的“马上乐”。那些羌笛、羯鼓、胡笳、琵琶,尽管与礼佛庆典不太协调,但在民族心态的驱使下,还是突破了佛教的约束和钟、磐、琴、瑟的诱惑,宁愿用本民族的偏好和自身的文化传统去取代那些“外来的”文化,以平衡他们的心态。
第三是鲜卑人在“汉化”与反汉化的心态斗争中,始终没有统一。孝文帝为推行汉化不惜迁都洛阳,不惜杀害反汉化的亲生儿子元恂。从历史发展观来看,孝文帝是进步的;但从民族心态来说,则是悖谬的。所以留守在平城故都的鲜卑遗老,可以不顾历史的潮流.极力维护其民族形象。在第三窟的三尊造像上,就体现了这种保护民族尊严的逆反心态,当龙门石窟的造像已经汉化之后,这里依旧按照他们业已承认了的“云冈风格”为废太子元恂凿琢了一躯更加完美的象征佛像。这件事大约发生在正光年间,而不是有些学者推论的发生在隋或唐初。六镇之乱,迫使这个洞窟的造像工程停止了,它也就成为云冈工程的终点。
4、使民俗特征以高雅的形式表达
云冈石窟的窟内总体布局反映的是民俗观念的伦理秩序。比如对一佛二胁侍或一佛四胁侍的排列,不仅突出中尊主座的地位,而且还从形体的大小上作了夸张的处理,一般中尊主佛要比两旁胁侍大出两三倍以至四五倍。这绝不单纯是为了渲染主佛的庄严,而是兼含着尊卑、主奴的等级伦理意义。这种形体大小的尊卑在人世间的现实生活中是不能体现的,尽管有此伦理的意思,但绝无如此的伦理形状。石窟文化却把抽象变为具象。由此推衍云冈石窟中一切陪衬雕饰.如供养人、力士,以至鸟兽、器物等,都在尊卑伦理的观念下,等级鲜明,大小有别,次第有序,美丑有格。陪衬就是陪衬,绝不许喧宾夺主。
民俗风情还寄寓在洞窟、佛龛的装饰上,民间的技巧用作点缀装饰。如三开间或单开间的民间住屋式的佛龛;窗框、门楣的花边装饰;平棊藻井的图案布局;供养人的跪拜仪态;乐舞伎的乐态舞姿;花卉鸟兽的吉祥取义等等。几乎都是民间的文化形式,而不是佛教文化的规定形式。再如塔,起源于印度的塔,到在民间工匠手中,就把那种单层覆钵式的形状,美化成多层楼堂殿阁式的建筑形状。云冈石窟中出现的有:大的如中心塔柱,刻出层次,极尽装饰之能,加上华美之饰;小的如壁面浮雕的多级式、重檐式、殿堂式、楼阁式的各种塔样,无不是民间的创作。
太武征伐西北时,虏掠了北凉的众多工匠并迁居平城,开凿云冈,这些工匠是主力.同时平城及京畿的工匠也是大量参加者。这样就把西北的、平城的民情风俗,自觉不自觉的留刻在云冈石窟之中。而云冈石窟也给这些工匠提供了极大创作场所。如各大型洞窟的三个壁面及窗框、门楣诸处。第十一窟东壁上部留下的“太和七年铭记”(是云冈极少的文字遗刻之代表)就说出了当时的情形.他们为给皇家、父祖祈求冥福而造像九十五躯,而贯串的意图就与皇家工程有所不同,这里是民间的意识,他们所要表示的是虔诚与敬仰,他们希望国泰民安,更希望父辈祖辈往生极乐世界。
5、使艺术特征独创,一格(云冈风格)
概括云冈石雕的艺术特色,大致是:粗犷豪放,大模大样,刀法洗炼,神韵安祥。其造像效果既富有写实的现实感,又富有传神的浪漫气。它是又熔理想与抽象于一炉,含真实与具象于一体的精美艺术珍品,是祖先心血的结晶,是文化艺术的瑰宝。
这些瑰宝、结晶、珍品的抽象风格,并不单纯是雕琢技艺,更主要的是构思的奇巧和手法的夸张。这里追求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
可以说云冈每一尊主佛在创作开始就要象征一位人物,那么该以佛像为主还是以人像为主?追求形似则将什么也不是。本来佛有三十二相的规范,而人则纷纷繁繁千姿百态,这是一组难以调和的比赋。云冈石刻却巧妙地解决了。最有代表性的县曜五窟的五尊大佛,乍看是佛,细审却又各具人态,很能引人追想当年拓跋力微、拓跋珪、拓跋焘、拓跋濬、拓跋后代(典型)的风姿。具有代表性的第二十窟大佛像,它综合了鲜卑人的共相,在佛的三十二相具备的基础上,又把人像味道浓浓溶入,既是一尊完美的佛像,又是一幅鲜卑人的典型肖像,且把鲜卑人装扮的那么美好。
据说印度阿旃陀石窟一号窟的释迦牟尼雕像,在面部展示了三种不同的表情,正面看是思维状,左侧看似拈花微笑,右侧看如悲悯众生。这种效果被誉为是艺术的魅力。云冈二十窟大佛似有更甚的艺术感染力,它以一派慈祥端庄静穆的庄严法相,把思维、微笑、慈悲、善良、亲切、端正等等优美的人间情感都集中溶汇在一起,而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也能突出表现某一个表情。⑿再加上淡淡的、微微的上翘的唇髭,⒀既渲染了佛的种性,又添几许活泼气息。至于整个造型,细眉长目、方直鼻梁、微翘U唇、垂肩双耳、宽肩细腰、透体僧袈、右袒肩臂、跏趺定印,等等雕琢技艺,无不为佛相、鲜卑种族像增添着光彩。如果说这就是云冈风格,那它的艺术特色就在于共相传神之中。显然他和炳灵寺石窟弥勒大像的苦修相,龙门石窟卢舍那大像的极乐相,天龙山石窟弥勒大像的空无相,敦煌莫高窟大佛的入定相⒁,判然分别。差别就是风格的体现。云冈风格,第二十窟大佛可为其嚆矢。
云冈风格,还有极尽夸张的民间审美观念贯串于其中。典型而又普遍的“两耳垂肩”造型可为代表。这种造型在佛像的三十二相中是没有的,仅在“八十种好”有“耳轮阔大成轮捶形”一好,也没说阔大到垂肩的程度。但民间流传着三国刘备有两耳垂肩的福相,工匠们就把它嫁接到佛像上。而这种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却又收到了美的效应。这也就是云冈风格的所在。龙门造像虽是云冈造像的延续,但风格不同,创新很大,起码这两个耳朵就收敛了不少。故而云冈风格是独立的。
6、使地理、历史两个特征极为明朗
就地理环境而言,云冈石窟与平城以西三十里(华里)之武州山是互为因果而相成者。武州山若不是灵岩与绝壁,石窟不会选择到那里,而云冈石窟不开凿在武州山,这灵岩圣地也持续不了那么长久。这明显地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相叠加。
通观国内现存石窟的选地,一般都选择偏僻幽深、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地方;对山水的要求虽然并不追求名山大川,但也要有神异灵气的圣地。武州山当时具备了这些条件。其实武州山的山势并不险峻,若从空中俯瞰,它的背后却是一派广袤的原野,并非崇山峻岭,严格地说,它仅是一段断崖岩岗。后世称之为云冈倒是恰如其份的。但此山岗的岩壁是一段整齐的绝壁,壁面又有过天然溶洞,岩石又是水沉砂砾结构,非常适宜开凿石窟,雕琢石像。再加武州川水从山脚下潺湲流过,不急不徐,河湾积水常能把山林景色倒映水中能构成郦道元看到的“林渊锦镜、缀目新眺”的美丽景致。从而完全具备了开窟造像的自然地理条件。当人文景观凿成后,武州山名声显赫了。
就历史时代而,当时中国北方正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人们求安心切,寻找精神寄托是当务之急。佛教在这方面恰能填补人们的精神空白,再加上一段灭法与复法的激荡反复,它的条件成熟了。北魏王朝集一朝的财力、物力、人力完成了此项丰功伟业,从而成为北魏的历史博物馆、地上文物、佛教圣地、艺术宝库,把北魏的文化状况汇集在这里。于是它最能体现北魏的时代精神。
云冈石窟的营建始末,文献上存在三种说法:早的是神瑞说,即所谓“始于神瑞(414年),终乎正光(523年)”⒂中的是兴安说,即“是年(兴安元年,453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晚的是和平说,即“和平初(460年),昙曜白帝,于京西武州山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⒃近年考古学者普遍承认和平说。我以为三说应当并存,因为各有端倪。概括而言:神瑞为发端,奠定了武州山灵岩地位;兴安为创始,始造“兴安石像”,为开雕琢石像先河;和平为实施,县曜五窟开工。几说并存较客观,不必咬定一点而忽视发展过程。莫高窟也有此问题,该是从司空索靖提壁仙岩寺算起?还是从沙门乐傅开窟一龛算起?或是从现存北凉洞窟算起?取舍不同,可以并存。对于“终乎正光”的说法争议较小,虽也有以为是指龙门石窟者,或以为言之无据者,但皆无足轻重。反正六镇之乱后,北地平城已经处于各族纷争的境地,战争、灾荒连年不断。北魏、北齐以至隋、唐,中央政权都已对它失去控制,石窟工程绝无延续条件,这是历史的实际。所以对终乎正光的说法勿庸质疑。那么云冈石窟从最早的神瑞说算起到在正光,时限都在北魏一朝。这样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历史特征就有集中表现一个朝代的特点,它与其他跨朝代的石窟又有不同。
综观云冈石窟在七种文化特征上的表现,充分说明:“石窟”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文化体。它以独特的文化形式表现着一时一地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它的价值是永恒的。
三、云冈石窟的文化价值
文化,就其价值而论,就在于它能以物质的具象或精神的抽象去标示人类文明进化的历程。而所有文化现象或文化遗迹,都不外乎是当时、当地的人类为了美化生活(物质的)和美化心灵(精神的)而遗留的文明痕迹。而所有的美化手段,又无非是创造一些身外之物去对自身之质进行文饰。所以评价文化价值,就不能脱离创造文化的动机与效果。
石窟文化是属于精神领域的文化,它标示着一代一地一族人的意识形态与宗教观念,也表现着全部的文化水准。同时,由于这些抽象的观念是通过石窟造形的有形实体表现的,故而也反映了物质文化。
鲜卑人留下的云冈石窟,蕴含着极高的文化价值。他们把一千五百多年前北魏兴盛时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凝重地熔铸于石窟之中,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从有形的实物去揣摩一个业已消逝的民族在其极盛时期的生活情景和精神面貌。
云冈石窟这种大规模、大气派;这种开创石窟与造像全部石雕化;这种风格鲜明的雕琢艺术;这种推进宗教社会化和神人合一的内蕴;这种掀起全国开窟造像之风的外延。其价值何在?归纳起来,它不仅在文化价值上有一定的份量,在此外的历史、考古、宗教、艺术、美学等诸方面,也有相当的价值。而其文化价值又体现在这诸方面的价值之中。这个精神文化体完全寄寓于它的物质文化形式中。
就其历史价值而论:云冈石窟可为北魏的实物史卷和形象史碑。北魏,这个神秘的鲜卑政权,究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何建树?社会发展到怎样状况?史虽有记,但语焉不详,尤缺形象实物以示其状。随着这个民族的消失,史学界更加渴求知其实情。云冈石窟可补此缺。无论其政治风云、经济实力、文化风格,这里都有形象的记录而且保存下来。它有直接表现者,有间接反映者,上溯可到拓跋远祖,下延可至北魏末期,内蕴思想意识,外显风土人情。从史学角度透过佛教形式剖析其史学内含,云冈石窟则是北魏的历史博物馆。
就其考古价值而论:云冈石窟作为地上文物是当之无愧的。考古学界已经注视了对它的艺术考古、分期考古。再引伸一步对它进行生活考古、意识考古,会拓宽很大的领域。比如石窟中的服饰、器物、音乐、舞蹈等,虽然是佛教的,但它的原型仍然是现实生活的,而且是当时、当地、民族的生活原型。它的那种生动、形象、翔实、细腻,有着极大的考古价值。云冈出土过一块“传祚无穷”瓦当能给考古带来很多的启示,面对如此丰富的地上文物应当带来更多的启示,何况所有一切造型与实物形状都包含着若干潜在的意识。运用综合、类比的分析方法必能考证出它的深层意识。云冈石窟的丰富资料给考古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它的考古价值大有发掘的余地。
就其宗教价值而论:云冈石窟标志着鲜卑人宗教观念的定型,并且把南北朝时期南方佛教与北方佛教的区分记录下来。鲜卑人的原始宗教是什么?尚不得而知。充其量也不过是萨满之类的巫神崇拜。当他们在南迁途中接触到道教、佛教以后,就开始了选择。与汉族统制者一样,一时是对两教兼容并信,一时又偏向一教,一时又偏向另一教。太武帝对佛教的灭法和文成帝对佛教的复法,是对佛教选择的一次大反复。随着云冈石窟的开凿标志着鲜卑人的宗教选择基本有了定向。佛教此后虽未成为国教,虽未独霸教坛,但已占了上风。说明鲜卑人对佛教与道教都有了深层次的了解,经过长时期的比较对佛教有了偏好,他们的宗教选择定型了。云冈石窟的佛教内容是佛教的,也更是鲜卑族的。这里记录着鲜卑人的佛教观念,它与同期南朝的佛教信仰就有很大的差异。研究云冈能增添中国佛教发展的内容。
就艺术价值而论:云冈的艺术价值是高品位的。前期研究者对云冈艺术零零总总提到许多精辟的评价。但对其艺术精髓的透视与品评.尚未达到综合完善的水平。究竟云冈艺术的精神何在?特征何在?人们虽已感觉到它是独特的,且命名日“云冈风格”,但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尚未找到准确答案。评价一种艺术是不容易的,可是云冈石窟有足够资料供研究者参照、对比、分类、组合,若能找出它的共性特征,则可接近真谛。
云冈石窟艺术集中于石雕工艺,石雕工艺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秦汉时期已有高水平的作品,到在北魏云冈石窟大兴石雕造像之风以来,石雕工艺达到一个高峰,无论是阴线刻划,还是圆雕浮雕,几乎都用大写意的手法,寓粗犷豪放于凝练,寓精细纤巧于洒脱,一派浑厚而又潇洒的手法。有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本土文化的基调,更多的是北方民族的气质与创造。它的价值在于划时代。
就美学价值而论:云冈石窟的艺术处在一个完美、系统、高水平的品位上,它的美学价值自然也是很高的。由于过去对艺术品评的不完善,给美学评价留下空白,现在已开始起步,应当使云冈的艺术哲学有所建树。
云冈美学的基础当归结在鲜卑人的审美观上。鲜卑祖先长期生活在“幽都之北”居处石室,与人类早期的穴居生活有共性,这正是他们的生活原型。以后虽经几代人的南下迁徙,直至建立国家,但对那个印象深刻的生活原型仍不易忘却。太武帝拓跋焘征服西北时,扩地千里,而最能引起他心灵共鸣的还是那草原牧野,依山傍水的洞穴而居的生活景象,所以他要派使臣去祭典幽都大石室。这就提醒研究者对鲜卑人的石室遗风应相当重视。在此基础上探索鲜卑人对石窟的审美观念,才不致脱节。云冈石窟的美学基础正在于鲜卑人的民族心态上。
云冈石窟之所以能超越河西、西域早期那种小型坐禅窟的格局,一下子创建出如此大型的、辉煌的、气势赫赫的大供佛窟,恐怕“石室”遗风的膨涨当推首要因素。至于那种大气派、大窟、大佛,以及粗犷、豪放、顶天立地、不可一世等风格,正是鲜卑人在他们的审美观念支配下,用以表示他们不甘心屈居于其他民族之下的一种民族心态的表现。
总之,无论云冈石窟的历史价值、考古价值、宗教价值、艺术价值、美学价值,都从一个侧面表现着它的文化价值。云冈石窟的主体价值在于文化。云冈石窟的文化价值,一言以蔽之:它是一个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一种精神文明的财富。它是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
注释:
⑴《水经注•氵纍水》。
⑵唐•张嵩《咏塞上诗》。
⑶金•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文。
⑷清•顺治十三年《重修大同镇城碑记》。
⑸《论语•雍也》。
⑹《魏书•序记》。
⑺⑻⑽⑾⒃《魏书.释老志》。
⑼北魏•高允《鹿苑赋》。
⑿《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载有二十窟主佛头像摄影十八帧,对比审视,可感到不同的情感内蕴。
⒀这唇髭,在一般照片上不容易看到,只有亲临像下方可。
⒁这几个像情的引喻.是我个人的体味,别人未必皆有同感。
⒂《大唐内典录》等。
(原载《北朝研究》1994.2—3合刊总第十五期云冈研究专号)